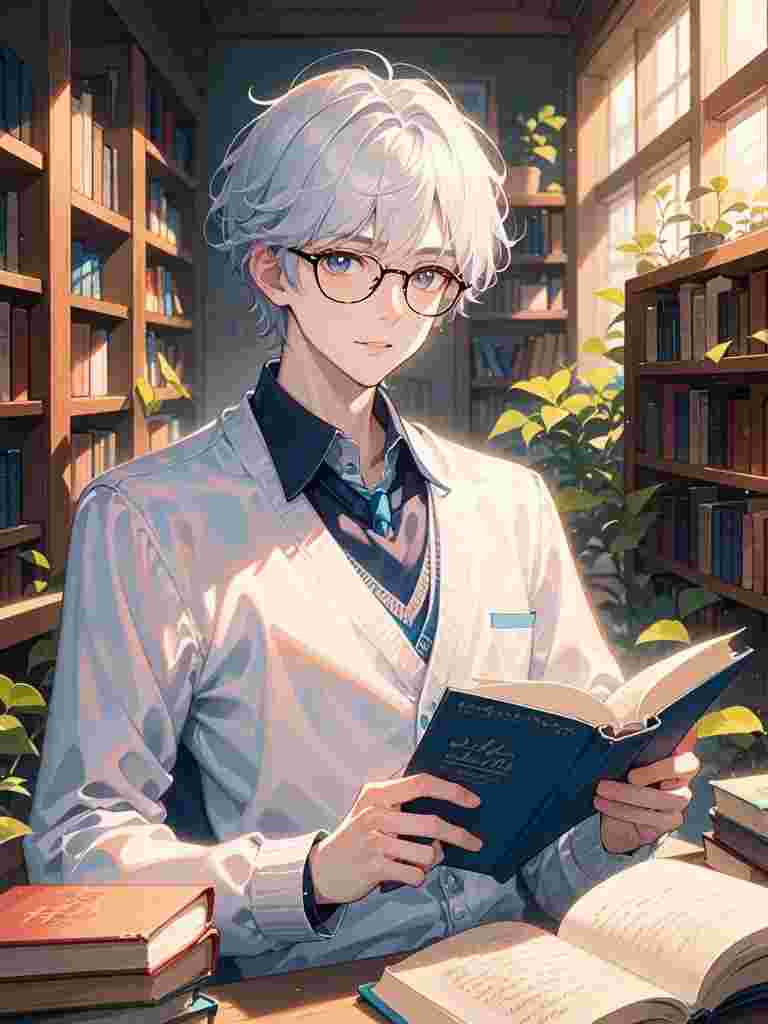我盯着“D37”愣神,那是江让在邮件里写过的车次。
广播突然喊:“D37 次开始检票。”
我心脏猛地跳了一下——不是今晚,是十几个小时后。
检票闸机刷身份证,“嘀”一声绿光。
我弯腰提箱子,余光瞄到隔壁通道一个背影:灰色卫衣、黑色鸭舌帽、拖着一个 24 寸旧行李箱。
那背影太像江让,我差点喊出声。
可人潮往前一涌,背影被淹没。
我安慰自己:眼花。
松城到京州 812 公里,他昨晚还在医院做康复陪护。
可脚还是不听使唤,逆着人流往回挤。
“小姐,请往前走。”
工作人员伸手拦我。
我隔着栏杆踮脚张望,却只看到无数顶相似的帽子。
站台上,列车员吹哨:“车门即将关闭!”
我被人流推上车,回头最后看一眼:玻璃门外,那个灰色卫衣的男生正好抬头。
鸭舌帽檐下的眼睛,一闪而过。
列车启动,铁轨发出“咣当咣当”的节奏。
我忽然不能呼吸。
07 车 12F,我的座位。
旁边 12E 空着,行李架却多出一个黑色双肩包。
包上挂着一个掉漆的小火车挂件——和我高二送江让的一模一样。
我伸手去摸,指尖发抖。
列车员过来检票,我一把抓住她:“请问 12E 有人吗?”
“有,刚补票,可能在别的车厢找座。”
我立刻起身,逆着过道往后挤。
05 车厢连接处,灰色卫衣男生正倚在车门边,低头看手机。
我隔着三米,嗓子发紧:“江让!”
他抬头,眼神里的震惊不比我的少。
“你怎么在——你怎么在——”我们同时开口,又同时停住。
列车晃动,我差点扑进他怀里。
他下意识伸手扶我,掌心滚烫。
“你不是今晚才——我改签了。”
“你妈——昨晚出院,我托给护工。”
他声音哑得像砂纸,“我想先送你报到。”
我盯着他,眼泪在眼眶打转。
“松工大的奖学金呢?”
“我申请延期一年,先休学。”
“你爸——跑了,但债务我认,等我慢慢还。”
他说得轻描淡写,却像在宣布一场漫长的战争。
列车驶过一片麦田,阳光照进来。
江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:京州大学新生住宿确认单,上面写着“江让(借住)”。
我瞪大

那天我没有等到他的微信小说
推荐指数:10分
小说《那天我没有等到他的微信小说》,此书充满了励志精神,主要人物分别是周放林苗苗,也是实力派作者“微辣是我最后的妥协”执笔书写的。简介如下:如果你也曾在夏天弄丢过一个人,请下翻。这一次,我们一起把“舍不得”写成“未完待续”。【第一章】6 月 24 号晚上,客厅像开考前 5 分钟那么静。我妈把风扇拧到三档,风呼啦啦吹,却压不住我心里的鼓。我把手机平放在茶几,屏幕停在“京招通”页面,刷新键都快被我摁出坑。突然,页面闪了一下——“查询通道已开......
第15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