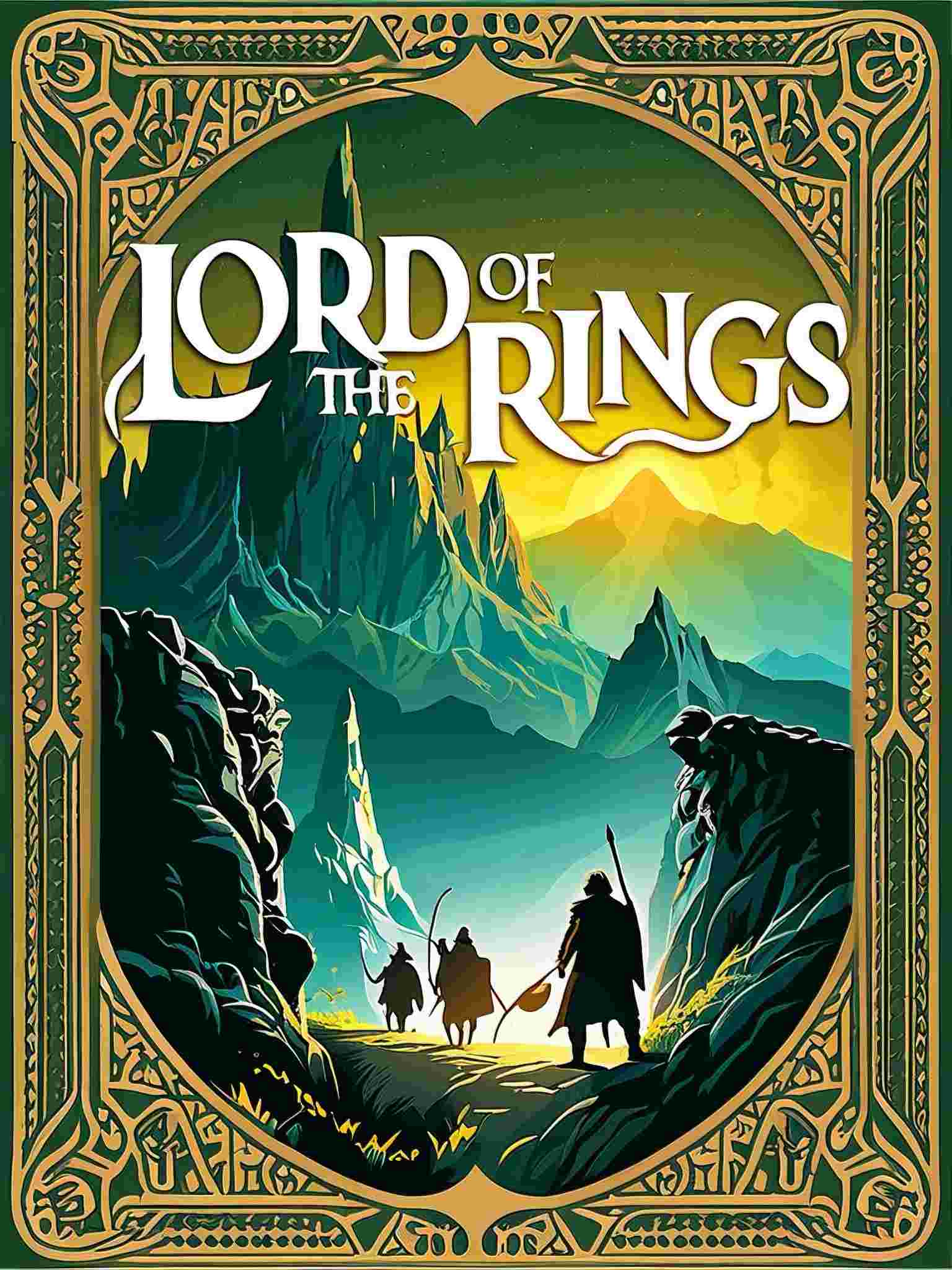哥的据点远,也安全。”
我捧着茶杯,眼泪掉进茶里,涩味混着清冽的甜,像我们这几年的日子。
“你知不知道,我在你‘坟’前坐了三天?”
我声音发闷,“上春山的桂花落了一地,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他把我揽进怀里,肩膀还是硬的,却比以前瘦了些。
“对不起,妍妍。”
他下巴抵在我发顶,声音带着颤,“我每次想跟你联系,都怕连累你。”
我们在榕树下坐了一下午,直到夕阳把茶山染成金色。
他跟我讲潜入时的事:假装在茶市和坤哥的人套近乎,跟着他们去边境走私,好几次差点被发现,全靠之前在警校学的本事躲过去;他还说,每次喝到白茶,就想起我在茶馆等他的样子,那是他撑下去的念想。
“警方已经掌握了坤哥的交易路线,”他握着我的手,掌心的薄茧蹭得我心疼,“下月初他们会在勐海的茶仓行动,到时候我会里应外合,等这件事结束,我们就找个小茶山,再也不分开了。”
我点点头,把脸埋在他怀里。
风里飘着茶香和桂花香,这一次,我不用再对着空荡的茶树下许愿,因为我等的人,终于回来了。
行动那天,我在义工站的屋里等他。
桌上放着他煮好的白茶,壶里的水早就凉了,我却不敢倒——怕他回来时想喝热的。
窗外的雨下了又停,直到深夜,门被轻轻推开,我回头看见他站在门口,脸上沾着点泥,左臂缠着绷带,却笑着朝我挥手:“妍妍,我回来了。”
我跑过去抱住他,他的胳膊有点疼,却还是用力回抱我。
“坤哥落网了,”他声音里带着点疲惫,却很轻快,“所有走私通道都被封了,以后再也没人能找我们麻烦了。”
那天晚上,我们坐在火塘边,他给我看警方发的表彰证书,上面写着“吴正同志,在打击跨境毒品走私案中表现突出,记一等功”。
他笑着把证书收起来:“这东西没用,不如跟你去种茶。”
半个月后,我们离开了云南,去了吴正早就找好的小茶山——在浙江丽水,离上春山不远,却更安静。
茶山脚下有间老房子,红砖墙,黑瓦顶,门口有棵老桂花树,是前房主留下的。
我们把大学时的照片挂在客厅墙上,把那个刻着“妍”字的茶罐放在

蓦然茶香张明妍妍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蓦然茶香张明妍妍全文》是作者““三川流”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,张明妍妍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读,主要讲述的是:风裹着茶山的冷意掠过衣领时,我回头望。他站在一丛半老的茶树下,灰衬衫被风吹得贴在骨头上,侧脸的轮廓明明像我藏在记忆深处的旧照片,却又隔着一层化不开的雾。他没看我,只望着远处翻涌的茶浪,眼神淡得像泡了十几遍的白茶,连风都吹不散那点沉底的寂。【1】下班拐进巷口时,总能看见那盏暖黄的灯。半年前这茶馆突然冒......
第15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