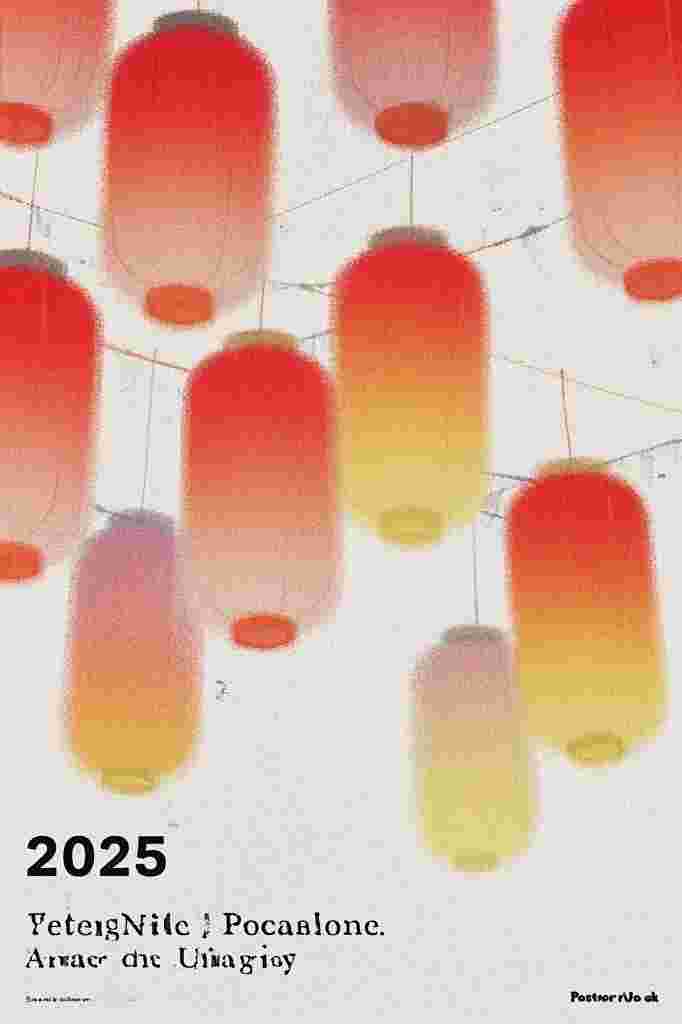阳光渐渐升高,照在地毯上,泛着刺眼的光。叶心心蜷缩在床角,抱着膝盖,看着窗外的雪山。雪山依旧壮丽,却再也引不起她的向往。她想起和陈阳约定的日照金山,想起手机里他焦急的声音,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
丹增说得对,她太不听话了。如果她乖乖吃饭,乖乖待着,不试图联系外界,是不是就不会连累卓玛?是不是手机就不会被摔碎?
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她掐灭了。不,她不能听话。一旦顺从,就再也回不去了。陈阳还在等她,孩子们还在等她,她必须撑下去。
只是那部碎掉的手机,像个沉重的预兆,压得她喘不过气。这是她和外界最后的联系,现在断了。她就像被扔进深海的孤岛,再也没人知道她在这里,没人知道她在等谁。
门外传来脚步声,停在门口。叶心心以为是丹增,立刻擦干眼泪,摆出防备的姿态。可等了很久,都没人开门。只有细微的摩擦声传来,像有人在门外放了什么东西。
脚步声渐渐远去后,叶心心走到门边,从门缝里往外看——是个小小的纸团,被塞进了门缝。
打开纸团,是卓玛歪歪扭扭的字:“叶老师别担心,我没事。手机我会再想办法,你一定要好好吃饭。”
纸团的末尾画着个笑脸,用红笔涂了圆圆的脸蛋,像卓玛每次送她的格桑花,带着笨拙却坚定的暖意。
叶心心把纸团按在胸口,听着窗外的风声,突然没那么害怕了。就算手机碎了,就算被关在这里,她也不是一无所有。至少还有人在偷偷惦记她,在为她想办法。
她走到桌边,看着卓玛早上送来的甜醅子。米粒吸足了糖分,在碗里泛着晶莹的光。她拿起勺子,舀了一小口放进嘴里。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散开,带着青稞特有的清香,像卓玛的笑容,像陈阳的承诺,像所有支撑她走下去的希望。
她要好好吃饭,好好活着。就算没有手机,就算联系不上陈阳,她也要等。等卓玛的下一次机会,等丹增放松警惕,等一个能逃出去的可能。
因为她知道,只要不放弃,希望就永远不会彻底消失。就像雪山不会永远被云雾笼罩,只要等,总有云开雾散的那天。
而她要做的,就是在那之前,好好活着。
门外的丹增站了很久。他听到了她压抑的哭声,看到了她捡起纸团的动作,也看到了她拿起勺子的瞬间。他攥着掌心碎裂的手机残骸,尖锐的边缘嵌进肉里,渗出血珠,却感觉不到疼。
这个女人,总是能轻易地让他失控,又能在不经意间,让他紧绷的神经松动。他以为摔碎手机能让她彻底绝望,能让她乖乖待在身边,却没想到,她总能找到新的支撑。
就像草原上的格桑花,就算被狂风暴雨摧残,只要有一丝阳光,就能重新挺直腰杆。
他转身往书房走,掌心的血滴落在地毯上,晕开小小的红痕,像朵无声绽放的花。他知道,这场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。而他和叶心心之间,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只是他不知道,这条路的尽头,到底是他想要的结局,还是两败俱伤的荒芜。
县城派出所的木门被风撞得吱呀作响时,陈阳正攥着那张被汗水浸透的身份证。柜台后的警察用藏语打着电话,搪瓷缸子在桌上磕出沉闷的声响,茶叶梗浮在水面上,像他此刻杂乱的心绪。
“同志,能听我说句话吗?”他往前探了探身,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
警察挂了电话,抬眼扫了他一眼。藏蓝色的警服袖口磨出了毛边,帽檐下的眼睛带着倦意:“你说吧,什么事?”
“我要报案。”陈阳的声音发颤,却努力保持镇定,“我女朋友被人软禁了,就在丹增的庄园里,我联系不上她,也进不去庄园。”
警察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,没说话,只是从抽屉里摸出个笔记本,慢悠悠地翻开。阳光透过木窗照进来,在笔记本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,衬得他的动作格外漫不经心。
“你女朋友叫什么?什么时候被软禁的?有没有证据?”他终于开口,笔尖悬在纸上,却没落下。
“她叫叶心心,是来这里支教的老师。”陈阳急切地说,“三天前我们被丹增请到庄园避雨,之后他就把心心关了起来,不让我们见面,还摔碎了心心偷偷联系我的手机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屏幕上还停留在通话失败的界面,“这就是证据,我们最后一次通话被强行中断了。”
警察瞥了眼手机屏幕,又喝了口茶:“丹增为什么要软禁你女朋友?你们认识?”
“不认识!”陈阳的声音陡然拔高,又很快放低,“他就是……就是看上我女朋友了,想用这种方式逼她留下。”
这话一说出口,柜台后的警察突然笑了。不是善意的笑,是带着点嘲弄的、了然的笑。他放下搪瓷缸子,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,看着陈阳的眼神像在看个不懂事的孩子。
“年轻人,饭可以乱吃,话不能乱讲。”警察的手指敲了敲桌面,“丹增在这地界是什么人物?他要是想留个人,用得着软禁?多少姑娘想嫁进他家庄园都没机会。”"

她去支教,却撞上霸总硬核求爱质量好文
推荐指数:10分
《她去支教,却撞上霸总硬核求爱》,是网络作家“叶心怡云桑”倾力打造的一本古代言情,目前正在火热更新中,小说内容概括:她满腔热血奔赴西藏支教,却一头撞进权势织就的牢笼。藏地雄鹰般的男人强势介入,以不容拒绝的姿态将她困在雪山深处。男友的退缩让她孤立无援,而他的步步紧逼更让她进退两难。原以为只是短暂的支教之旅,却成了无法逃脱的纠葛。她恨他的霸道,却又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滋生依赖。当温柔与压迫交织,自由与禁锢拉扯,她该如何挣脱这场高原困局?...
第3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