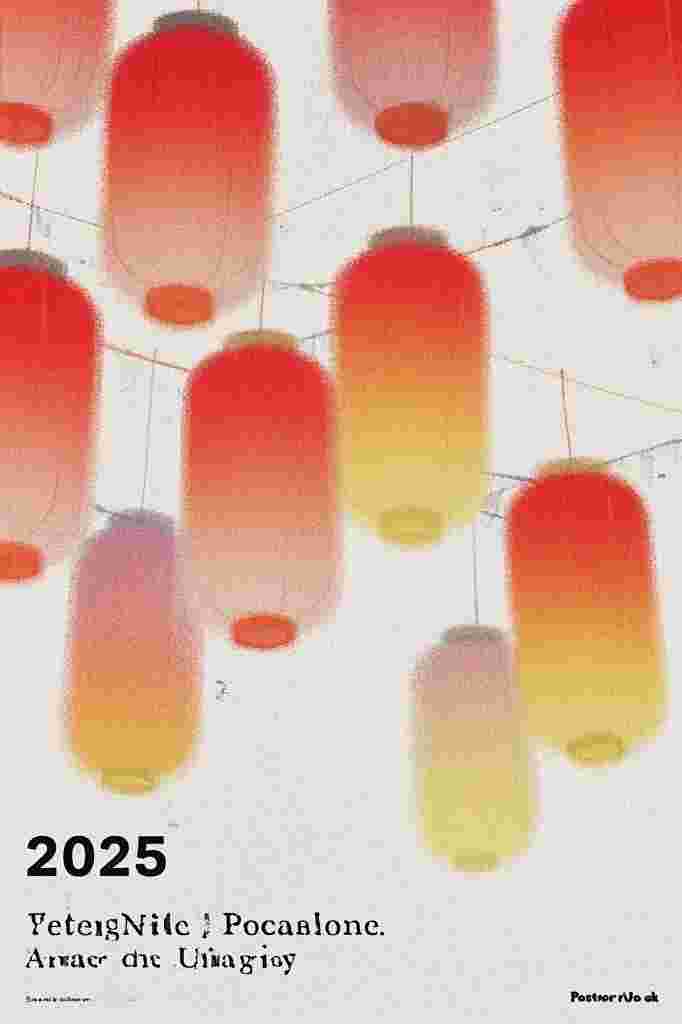“没什么,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”叶心心的声音很轻,像怕被风偷走,“陈阳,我今天在草原上看到好多野花,紫色的,像星星一样。”
“是吗?那一定很漂亮。”陈阳的声音温柔下来,“等你回来,我带你去看薰衣草田,比这个还好看。”
“好啊。”叶心心笑着点头,眼眶却有点发热。她握着手机,看着远处渐渐暗下来的草原,突然很想告诉他颈间的项链,告诉他那个强势又温柔的男人。
可话到嘴边,又咽了回去。她怕他担心,怕他胡思乱想,更怕自己说不清这复杂的心情。
“早点休息吧,别太累了。”陈阳的声音带着疲惫,“我明天还要早起开会。”
“嗯,你也早点睡。”叶心心说。
挂了电话,手机屏幕暗下去,映出她有些迷茫的脸。远处的经幡在夜色里猎猎作响,像在诉说着什么。叶心心摸了摸抽屉的方向,那里藏着一条蓝得像天空的松石项链,也藏着一个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秘密。
草原的夜来得快,星星很快缀满了天空。叶心心站起身,回了宿舍。她不知道,在学校围墙外的老槐树下,次仁正对着对讲机低声说着什么,而对讲机那头,丹增晋美的声音沉稳地传来:“她收下了吗?”
“收了,不过好像不太情愿,回来就摘下来收起来了。”次仁如实回答。
对讲机那头沉默了几秒,才传来一声低沉的“知道了”,随即便是忙音。
丹增晋美放下对讲机,看着远处校舍里亮起的灯光。那扇窗户里的身影,像一颗落在草原上的星星,遥远,却又充满了吸引力。
他知道她在抗拒,可那又怎样?草原上的雄鹰要捕猎时,从不会在意猎物愿不愿意。他想要的东西,迟早都会属于他。
夜风卷着草屑掠过他的藏袍,腰间的松石小刀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他抬手摸了摸腰间的佛珠,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。
游戏,才刚刚开始。
晨读的琅琅书声刚漫出教室,叶心心就攥着那条松石项链站在了宿舍门口。初秋的风卷着草叶掠过脚踝,带着牧场清晨特有的清冽,可她掌心却沁出了薄汗——银链被体温焐得温热,嵌在松石边缘的银花硌着指腹,像一枚必须归还的印记。
“老师,你要去找次仁叔叔吗?”卓玛抱着作业本经过,红绳辫梢扫过叶心心手背,“我刚才看到他在操场边喂马呢。”
叶心心点点头,把项链往帆布包里塞了塞,布料摩擦的窸窣声里,藏着她一夜未平的心事。昨夜她对着抽屉里的项链坐了半宿,月光透过窗棂落在松石上,蓝得像化不开的夜色。她数着羊油灯跳动的火苗反复想:这东西太贵重,也太烫手,必须还回去。
穿过操场时,次仁正蹲在黑马旁边,手里捧着铜盆给马刷毛。黑马见到叶心心,打了个响鼻,前蹄轻快地刨了刨地——它鬃毛上还系着丹增晋美特意编的红绳,和卓玛辫子上的颜色如出一辙。
“叶老师。”次仁直起身,羊皮坎肩沾着草屑,“今天怎么起这么早?”
叶心心没绕弯子,从帆布包里取出项链递过去:“次仁,麻烦你把这个还给丹增先生。太贵重了,我不能收。”
铜盆里的水还在轻轻晃荡,映出松石在晨光里的蓝。次仁的目光在项链上顿了顿,没接,反而往后退了半步,双手在藏袍上蹭了蹭:“叶老师,这是丹增特意让银匠打的,你这么送回来,他会不高兴的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你别为难我了。”次仁挠了挠头,黝黑的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,“昨天他送你项链的时候就说了,要是你不肯收,或是悄悄还回来,我这个月的工钱就没了。”他指了指黑马,“这马的马鞍还是我攒钱刚换的呢。”
叶心心捏着项链的手指紧了紧。她知道次仁不是说谎——丹增在牧场的威望无人能及,说一不二的性子连乡干部都要让三分。可让她戴着这条价值不菲的项链,总觉得像被无形的线捆住了手脚。
“这不是钱的事。”她把项链往前递了递,“你就告诉丹增先生,心意我领了,但礼物真的不能收。我是来支教的,不是来要东西的。”
次仁却像被烫到似的往后躲:“叶老师,你是不知道丹增的脾气。”他压低声音,眼神往四周扫了扫,“他认准的事,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上次牧场的老阿爸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,他没看上,直接让人把聘礼扔到了河里——他不想收的东西,谁也塞不进去;可他想给的东西,没人能退回去。”
叶心心愣住了。她看着次仁认真的脸,突然想起丹增递项链时那双深邃的眼睛,想起他按住自己肩膀时不容置疑的力道。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闷得发慌。
“可是这太贵重了。”她还想争辩,指尖的松石却凉得像块冰。
“在丹增眼里,这不算什么。”次仁笑了笑,露出两排白牙,“他牧场里的牦牛有几百头,去年挖虫草卖的钱,够盖三个这样的学校。再说了,这松石是他自己去山涧里采的,说是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适合你。”"

她去支教,却撞上霸总硬核求爱无删减版
推荐指数:10分
主角是叶心怡云桑的古代言情《她去支教,却撞上霸总硬核求爱》,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古代言情,作者“小妖姨”所著,主要讲述的是:她满腔热血奔赴西藏支教,却一头撞进权势织就的牢笼。藏地雄鹰般的男人强势介入,以不容拒绝的姿态将她困在雪山深处。男友的退缩让她孤立无援,而他的步步紧逼更让她进退两难。原以为只是短暂的支教之旅,却成了无法逃脱的纠葛。她恨他的霸道,却又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滋生依赖。当温柔与压迫交织,自由与禁锢拉扯,她该如何挣脱这场高原困局?...
第13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