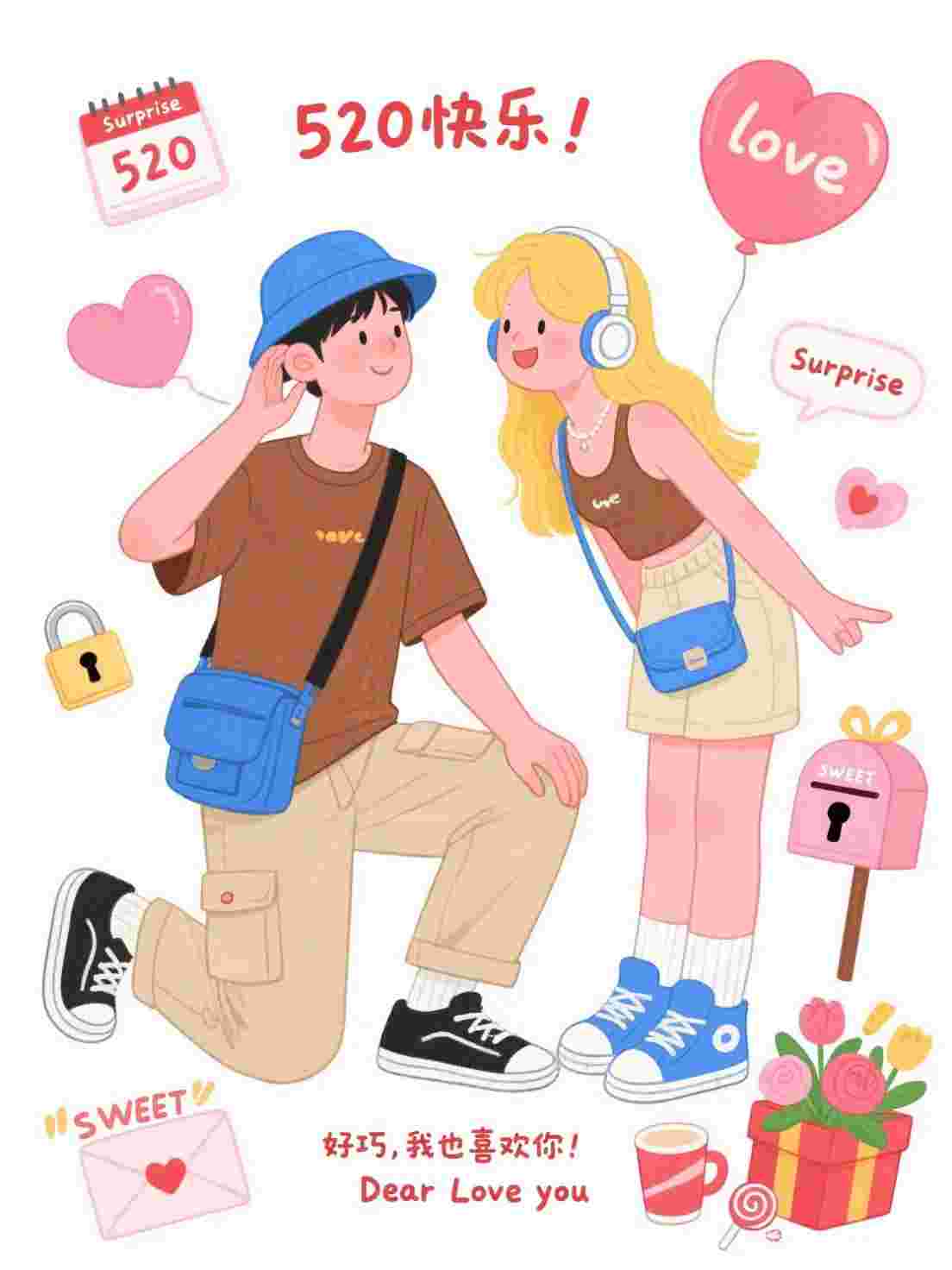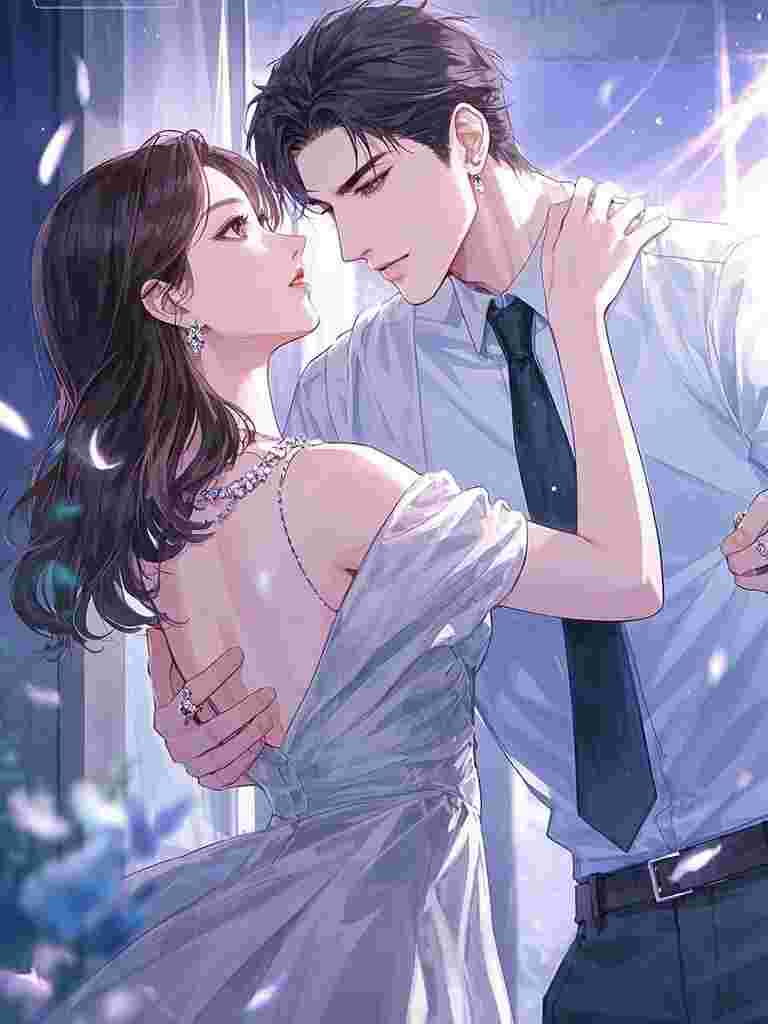卖得如此彻底,彻底到连最后栖身的四间正屋也没留下,这是任谁也想不到的事情。
十几口子一家人,老老小小无处去,先是借住村西家庙里,可是家庙的房子年久失修,根本待不下去。
丁花到村里打探了一下,有户人家愿意帮他们,但不能进院子。
丛家老小只得蜷缩着借住在人家的大门过道里,夜里过道的穿堂风是很冷的,那种冷是刺骨的感觉。
已经被大烟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丛欣,裹着一件不知哪里淘换来的破棉袄蜷在草席上,烟瘾刚过,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满足,对旁边唉声叹气的丁花嘟囔着:“愁什么?
借钱吃海货,不算不会过,会有法子的,我就不信,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”
至于邻人的嗤笑声,丛欣就更不在意了,别人笑,他也笑,他乐观的理由依然源自那句口头禅:借钱吃海货,不算不会过。
丁花却更加沉默了,每天在黑暗里无助地睁着眼,听着儿女们压抑的抽噎声,她只觉得这条硬硬过道冰冷的砖地,正一点点吸尽她最后的热气。
二战火终于烧到了昌阳。
鬼子来了,城关村乱成了一锅粥。
丛欣一家老小像被惊散的蚂蚁,裹在逃难的人潮里仓惶奔往烟城。
他们一路风餐露宿,个个蓬头垢面,活像一群叫花子。
那点仅剩的“半衙”气派早在滚滚的黄尘中和饥饿的窘迫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一天,他们来到一个破败的村口歇脚,不曾想,竟在这里撞见了同村的郭宏伟。
郭家早年也败落过,但后来凭着郭宏伟在烟城做点小生意,家境慢慢好了起来。
此时的郭宏伟虽然也在逃难,但却一点不像落难的样子,穿着体面的长衫,头也梳着油亮。
看到丛欣一家蜷缩在墙角啃着硬如石头的窝头,郭宏伟的眼神复杂起来。
他走到丛欣面前叹了口气,扫了几眼丛欣身后那群瘦骨伶仃、眼神惊恐的孩子,目光最后落在那个最小的、约莫七八岁、衣衫褴褛的小丫头身上。
郭宏伟指了指她对丛欣低声道:“老丛啊,你这拖家带口的逃难不易。
如今,你们家也就剩这点……还值点钱了。”
郭宏伟的声音不高,说出的话却句句扎人,狠狠扎进了丛欣的身子里,刺穿了他浑浊麻木的神经。
那时的他,正下意识地

残香如梦丁二全丛家小说结局
推荐指数:10分
最具实力派作家“沙月新”又一新作《残香如梦丁二全丛家小说结局》,受到广大书友的一致好评,该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丁二全丛家,小说简介:一丛家是昌阳城最大的富户,上数三代人都是本地有名的乡绅。、可到了第四代就不行了,丛家老小坐吃山空不说,仅丛大少爷一个人,就把家产赌得望见边儿了。这不,刚进腊月门,外边的风都刮了两天两夜了,丛大少爷仍然泡在赌场里,对外边的事情,不管不问。天蒙蒙亮时,丛欣丛大少爷才裹起那件油光水滑的狐裘,从热气腾腾的赌......
第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