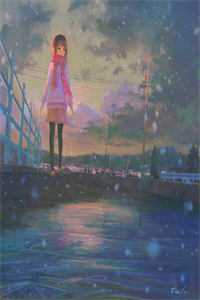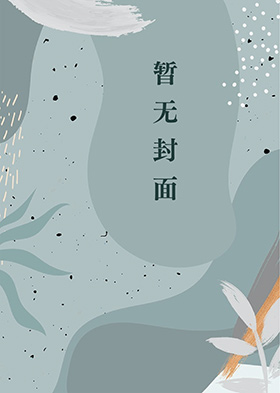来的、无比讽刺的祭奠。
开展当天,宾客如云。
我隔着人群,一眼就看到了沈聿白。
他没有与任何人交谈,只是独自站在作品《断簪》前,久久未动。
那支断裂的金簪,一半是繁复的唐代宝相花纹样,一半是冰冷的现代极简线条。
它象征着我们断裂的情感,也象征着我重生的自我。
这是我所有作品里,最私人的一件。
他的学生,也是他后来的妻子林婉清,悄悄走到他身边,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:“你写序的时候,是不是……哭了?”
他没有回答,只是挺直了本有些佝偻的背。
轮到我上台致辞,无数镜头对准了我。
有记者高声提问:“苏晚老师,很多人都想知道,您恨那个曾经全盘否定您的人吗?”
我握着话筒,目光越过人群,直直看向沈聿白,微笑着摇了摇头:“我不恨。
因为他让我明白——真正的光芒,从不需要仰望他人的眼睛来点亮。”
闪光灯爆闪的瞬间,我看见沈聿白决然地转过身,挤出人群,那背影仓惶得像个打了败仗的老兵。
也就在那一刻,口袋里的手机嗡嗡震动。
是佳士得的Ms. Rossi发来的新消息: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想收藏《锈金》全套。
苏,你的名字,要进史册了。”
我抬头望向展厅穹顶的光,轻声说:“这一次,是我要你仰望我了,沈教授。”
我以为,这就是故事的终章。
一个关于破碎与重生的,完满句点。
可我没想到,展览开幕后的第三天,798的风向,就彻底变了。
7我站在展厅侧廊,指尖悬在《破塔》系列的光影投影控制器上,细微调整着断壁残垣上流淌的数字光斑。
导览员清亮的声音穿过人群,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崇敬,正对一群金发碧眼的访客讲解:“这件《断簪》,灵感来自一位中国教授未发表的手稿——但他本人,从未将其视为艺术。”
我的指尖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,没有回头。
一只手递过来一部平板,陈导压低声音,难掩兴奋:“看看这个。”
是《亚洲艺术》(ArtAsia)的电子稿截图,封面给了我那枚用沈聿白丢弃的领带夹改造的《锈金·权戒》一个惊人的特写,冰冷的金属在镜头下折射出一种近乎残酷的美。
标题加粗放大
沈聿白林婉清《别了,我的象牙塔教授后续+全文》全文免费阅读_别了,我的象牙塔教授后续+全文全集在线阅读 试读

别了,我的象牙塔教授后续+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别了,我的象牙塔教授后续+全文》震撼来袭,此文是作者“银白色那尾鱼”的精编之作,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沈聿白林婉清,小说中具体讲述了:推荐语:有没有一种感觉,你倾尽所有去爱一个人,最后却发现,你的热爱、你的事业、你的一切,在他眼里都一文不值?我曾是沈聿白最忠实的信徒。他是最年轻的艺术史教授,我崇拜他到将他晦涩的论文奉为圭臬,甚至为他放弃了去法国留学的名额。我以为我们是灵魂伴侣,直到我将毕业设计——一枚融合了他论文中冷门文物元素的领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