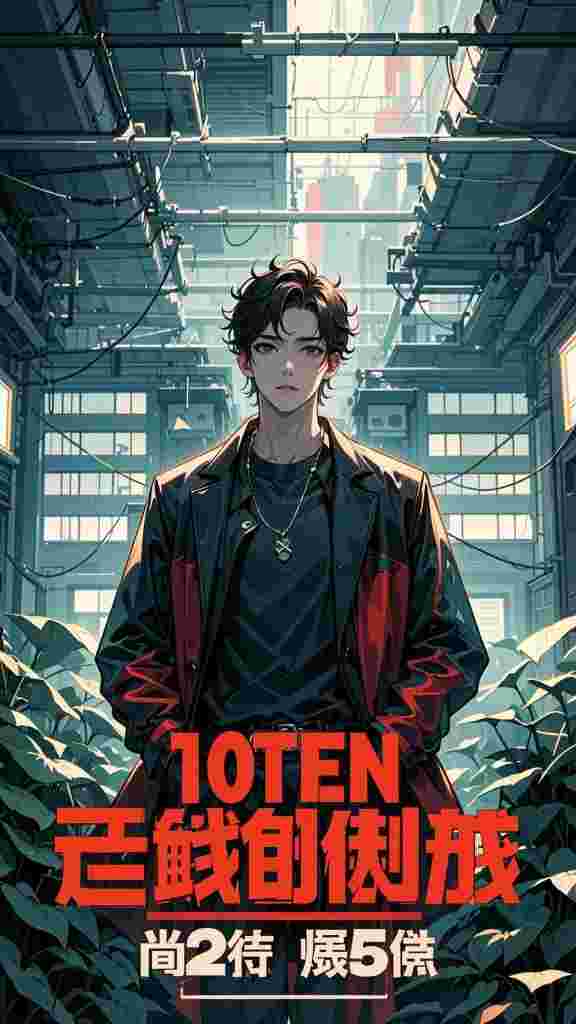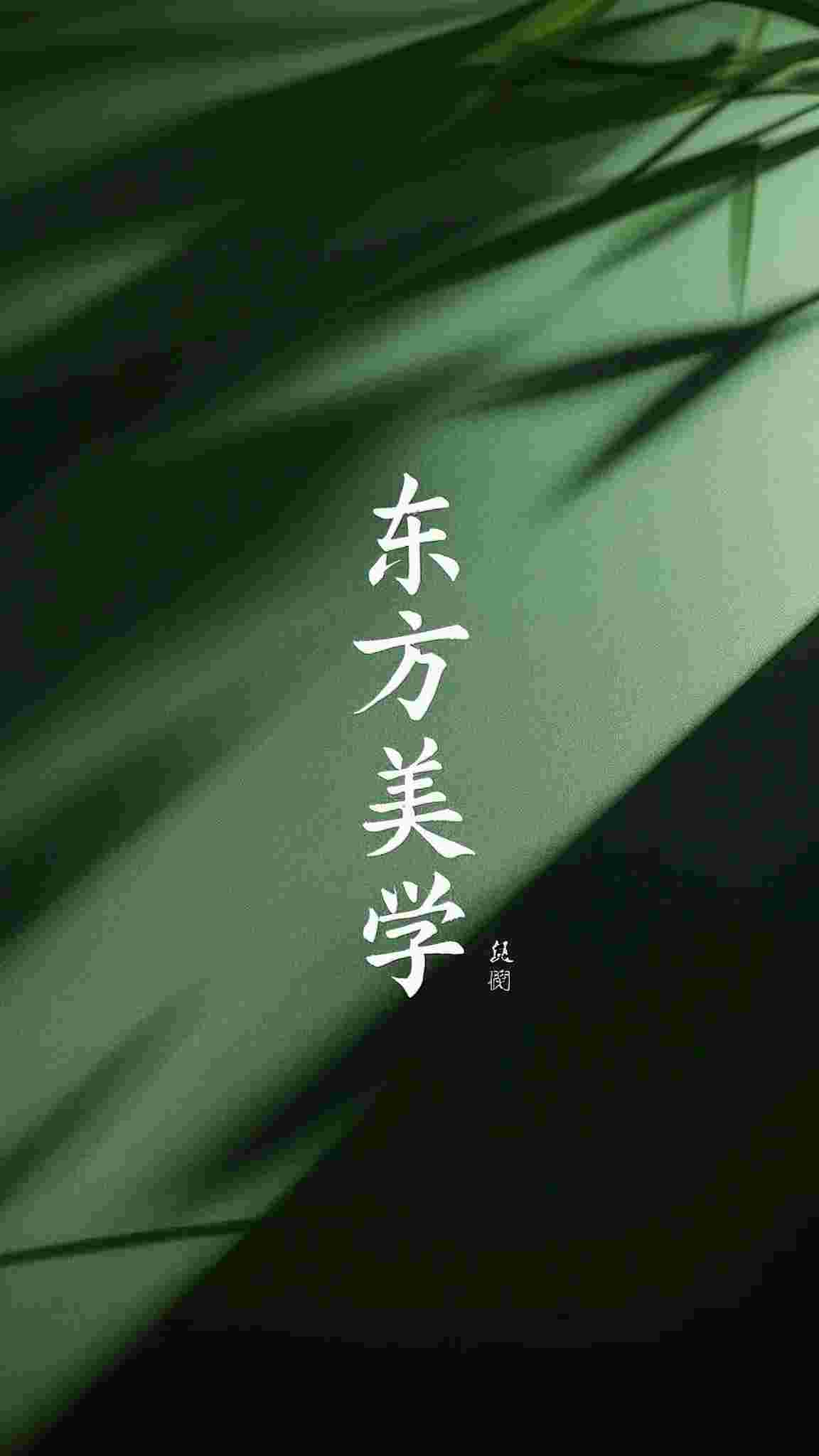记本,一笔一划记着老人的话。
阳光落在他身上,没了当年京圈太子爷的倨傲,倒像个认真听故事的学生。
深秋的巴黎下了场小雨,工坊的门没关,风吹进来,带着树叶的清香。
我坐在窗边,看着墙上的名字,突然听见有人喊 “Lune 姐”—— 是阿雅,她穿着绣着 “阿雅” 的舞蹈服,身后跟着一群孩子,他们手里拿着舞蹈节的金奖证书,证书上写着 “《我的名字》, 献给所有敢说‘我是谁’的人”。
孩子们在工坊里跳舞,后背的名字随着动作轻轻晃动,像跳动的星星。
我看着他们,想起在巴黎地下工坊的血与灰,想起谢临的系统围剿,想起无数个在名字里找到力量的人。
原来,所有的抗争都不是为了自己,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笑着写下自己的名字,像苏晓的小太阳,像铁蛋的果树,像赵卫国的誓言。
雨停了,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墙上,那些名字在月光下闪着光。
我拿起蜡笔,在空白处写下 “林晚”,旁边画了个小月亮 —— 这是我给自己的约定,也是给所有寻找名字的人的约定:只要还有人需要,这里永远为你留着一块地方,用来写你的名字。
第七章:蜡笔与星光“身份博物馆” 的春季特展 “名字的温度” 开展前,我收到了个特殊的包裹, 来自汶川的快递箱,里面装着阿雅舞蹈教室的孩子们绣的名字布偶,每个布偶的胸口都缝着孩子的名字,针脚歪歪扭扭,却格外认真。
附信里,阿雅说:“孩子们现在会在舞蹈服上绣自己的名字,有个孩子以前总被叫做‘哑巴’,现在会指着名字说‘我叫安安,会跳舞’。”
我把布偶摆在特展 C 位,旁边放着苏晓的蜡笔画,画里的 “苏晓” 旁边多了好多小太阳,是她和同学们一起画的。
开展当天,展厅里挤满了人,有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在 “无名墙” 前站了很久,他手里拿着张泛黄的纸,上面写着 “张桂兰,1947.06.12,织了一辈子毛衣”。
“我以前总觉得,我的名字不重要,” 老人笑着说,“现在才知道,就算我不在了,我的名字还能留在这,多好。”
周明带着 “名字库” 的新数据来展厅,

我退婚后,京圈太子爷疯了京圈陆沉舟(番外)+(结局)
推荐指数:10分
最具潜力佳作《我退婚后,京圈太子爷疯了京圈陆沉舟(番外)+(结局)》,赶紧阅读不要错过好文!主人公的名字为京圈陆沉舟,也是实力作者“豆娘X4”精心编写完成的,故事无删减版本简述:《我退婚后,京圈太子爷疯了》导语:我是林家养女,十八岁那年,京圈太子爷陆沉舟亲自来提亲:“林娇娇,等你十年了。” 我感动不已,甘愿为他放弃留学机会,留在他身边。 可真千金归来那天,他当众撕毁婚书:“抱歉,我认错人了,她才是我青梅。” 我心碎退婚,远走国外。 五年后,我在巴黎时装周封神,他却跪在我工作......
第12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