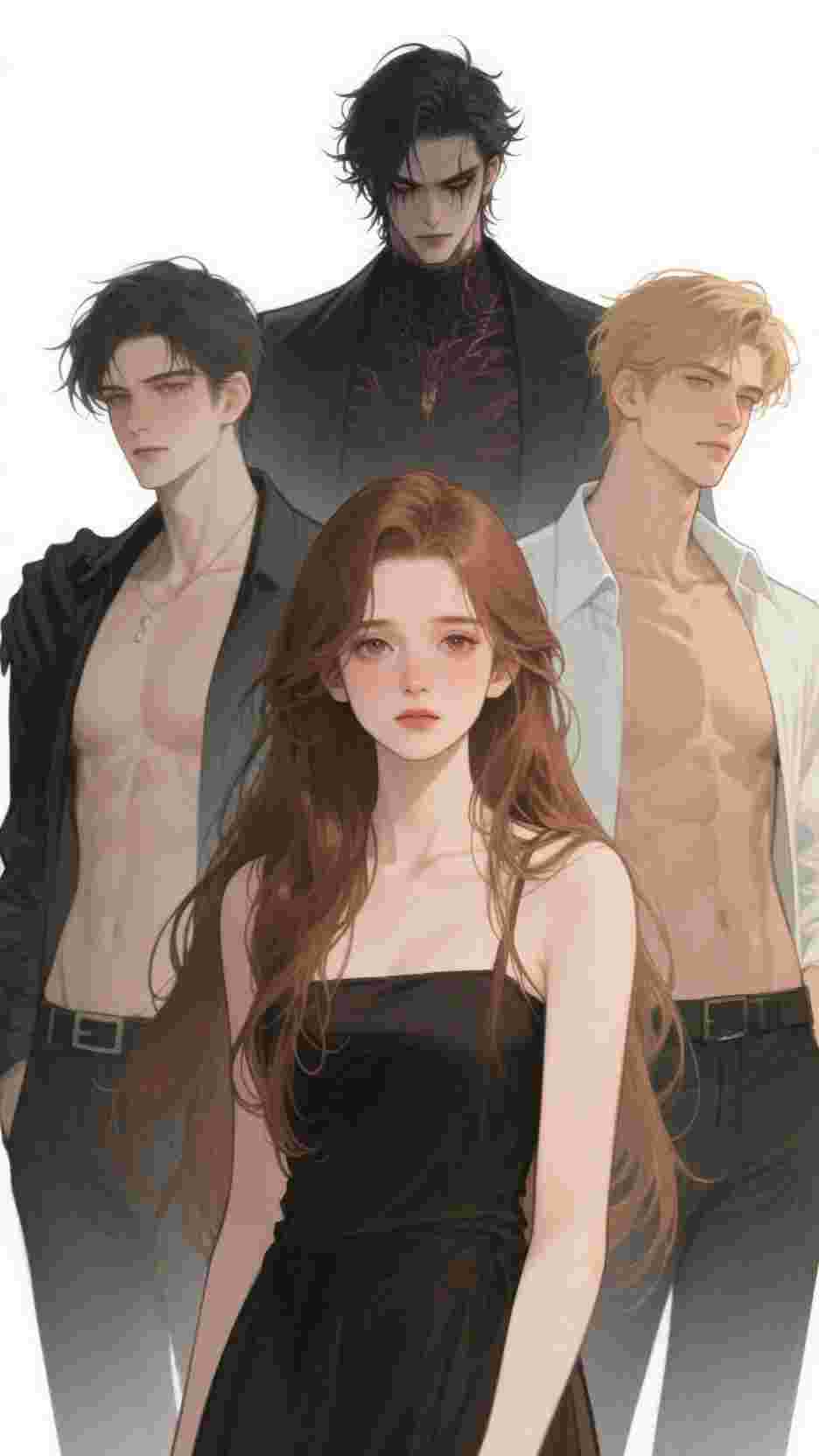离交通线的深山。
流量!
话题!
独家!
一个个炽热的词汇在我脑中炸开,这足以让我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,让所有质疑的人闭嘴。
理性的警铃微弱地响了一下——这太贸然了,对方身份不明。
但被数据煎熬的焦虑和成名的渴望,像一只更强大的手,将那点疑虑狠狠摁了下去。
三天后,我站在了雾隐村的入口。
村子比想象中更破败闭塞,几十座木屋像被随意丢弃的积木,散落在浓得呛人的山雾里。
手机信号在这里只剩下微弱的一格,时有时无。
几个蹲在村口石磨旁抽烟的男人停下交谈,浑浊的眼睛毫无顾忌地上下打量着我。
目光里没有好奇,只有一种近乎敌意的审视和排斥。
我挤出博主惯用的、表示友好的笑容,换来的只有更冷的沉默和扭头。
唯一的突破口是村支书,一个面色蜡黄的中年男人。
我说明来意,但是隐去了山魈,只说是做民俗采风,村支书皱着眉喊来一个老人。
“这是赵伯,村里老户,你要问老的传说,找他。
不过......”村支书顿了顿,语气硬邦邦的,“后山那片林子,别去。
不是你们城里人逛的山。”
赵伯佝偻着背,他沉默地带着我去临时落脚的空屋,一路无话。
直到我试探着问起“山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......动物?
比如,长得有点像人的?”
赵伯的脚步停住了,他缓缓转过头。
那双蒙着一层白翳的眼睛盯着我,让我脊背莫名一寒。
“女娃。”
他声音沙哑,“山里东西多了,不见得都是给人看的。”
“有些老话,听了就得当真。
不该去的别去,不该招的别招。”
他目光似无意地扫过我身上那件亮红色的防风衣:“尤其是外姓人。”
屋外,天色迅速暗沉下去,山雾更浓了,几乎吞没了远处的屋脊。
我坐在冰冷的炕沿,手机上,“山民”的信息又来了:“林老师到了吗?
晚上是最好的时机,那东西常在后山坳那棵老槐树附近活动......我白天不便露面,晚上林口等您?
机会难得。”
后面紧跟着一张更清晰的局部特写——一只覆盖着暗褐色粗毛的巨大爪子,指甲厚钝而肮脏,死死抠进树皮里。
诱惑力压倒了恐惧和警告,流量就是一切。
我回复:“

山魈的邀约赵伯热门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热门小说《山魈的邀约赵伯热门番外》近期在网络上掀起一阵追捧热潮,很多网友沉浸在主人公赵伯热门演绎的精彩剧情中,作者是享誉全网的大神“遗愿传承”,喜欢现代言情文的网友闭眼入:为冲破事业瓶颈,身为民俗博主的我只身前往与世隔绝的雾隐村,追寻一个名为“人面山魈”的诡异传说。起初,一切都很顺利。一位自称“山民”的热心粉丝为我远程指引,我成功拍到了令人颤栗的模糊影像,流量随之暴涨。直到我回看一段惊险逃生的素材时,才在画面角落看清。那个一直为我指引方向的“山民”,就站在禁地最深处,......
第2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