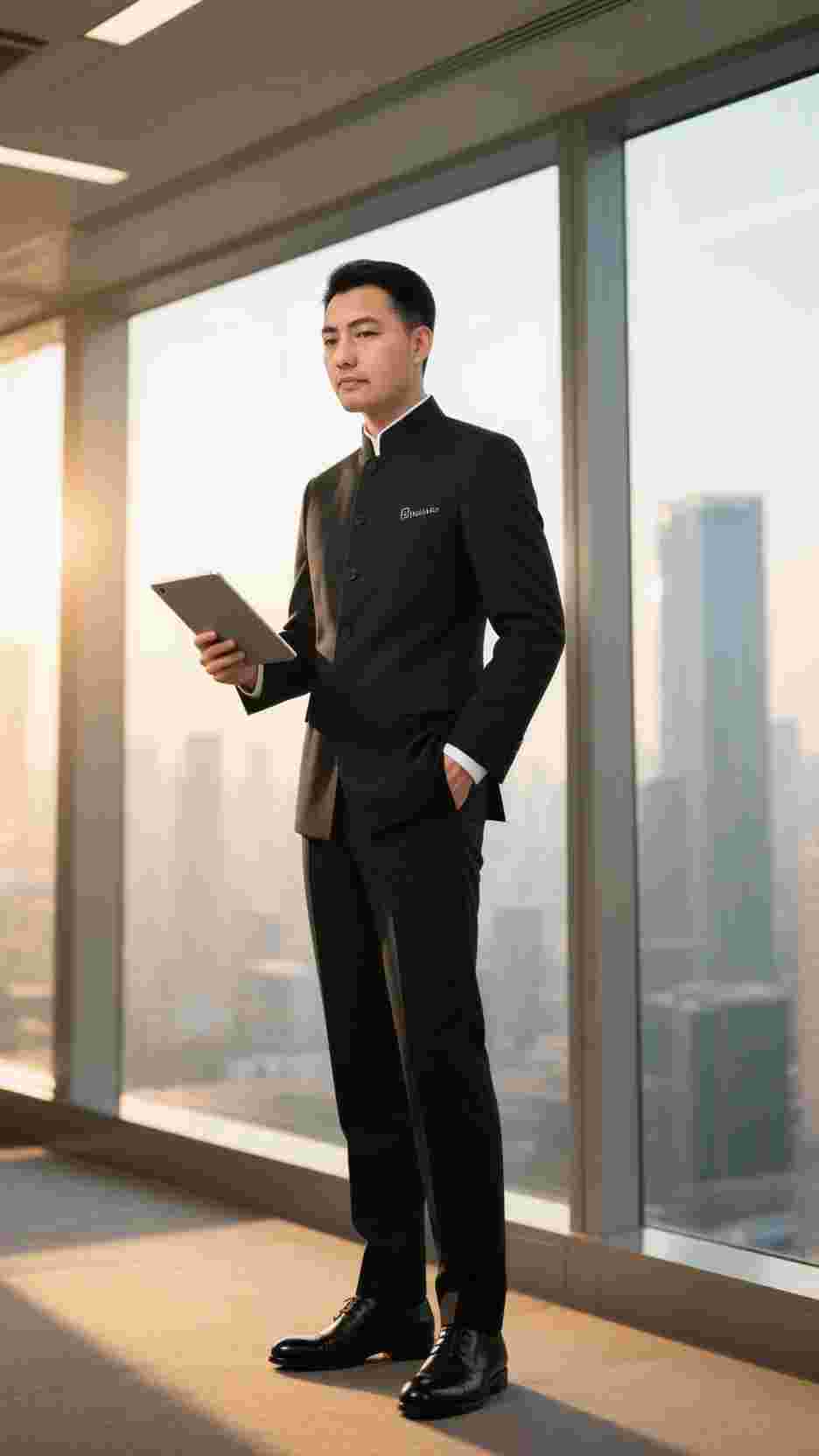混杂着某种滚烫的液体,让他整个人看起来破碎又可悲。
“念衾,我不是不要你,是我蠢,蠢到以为你永远都会在。”
苏念衾始终没有开门请他进去的意思。
她只是沉默地从屋里搬出一张矮桌,放在廊下。
然后是炉,是壶,是茶具。
炭火烧旺,壶里的水咕嘟作响,白雾升腾,模糊了她平静无波的脸。
她慢条斯理地投茶、洗盏、注水,一套动作行云流水,仿佛门外那个撕心裂肺的男人,不过是这场梅雨季里一道无关紧要的背景。
最后,一杯滚烫的碧螺春被她素白的手指推出,停在桌子中央,正对着沈司衡的方向。
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接,指尖即将触碰到温热的杯壁。
“沈先生,小心烫。”
她终于开口,声音清清淡淡,像杯中的茶雾,一吹就散。
沈司衡的手猛地僵在半空。
那股灼人的热意仿佛穿透了瓷杯,从他的指尖一路烧到心脏,烫得他狠狠一哆嗦。
他抬起头,看到的却是她投向巷口的目光。
那里,周砚舟撑着一把黑伞,静静地看了这边几秒,最终,一言不发地转身,融进了更深的雨夜里。
苏念衾收回视线,望着门外那个仿佛被钉在原地的身影,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,轻啜了一口。
茶水微苦,而后回甘。
她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。
有些火,烧得再旺,也只能照亮一片废墟。
夜越来越深,雨声里,只剩下壶水不知疲倦的沸腾声。
屋檐下的人没有走,屋里的人也没有再开口。
4雨停了。
天光乍破,青石板台阶上湿漉漉地淌着水,也淌着昨夜一夜的纠缠。
烬庐的门槛前,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双男士皮鞋,昂贵的意大利手工货,此刻却像两条被遗弃的落水狗,鞋尖固执地朝向门内,鞋头皮面被雨水泡得起了皱,仿佛曾有人穿着它,在这里跪了许久。
苏念衾从工作间出来时,晨光正好落在鞋上,反射出狼狈不堪的光。
她看都没看一眼,只对外间的学徒淡淡吩咐:“把那双鞋收进杂物间最里面的角落,别碍事。”
学徒应了声,小心翼翼地用布包起那双鞋,像在处理一件沾了晦气的旧物。
苏念衾一夜未眠。
倒不是因为沈司衡在门外压抑的哭声和一遍遍的“念念,开门”,而是那场雨,让她猝不及

我的爱意在燃尽后沈司衡苏念衾番外+无删减版
推荐指数:10分
沈司衡苏念衾是现代言情《我的爱意在燃尽后沈司衡苏念衾番外+无删减版》中涉及到的灵魂人物,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,作者“银白色那尾鱼”正在潜心更新后续情节中,梗概:推荐语:我花了三天三夜,将男友沈司衡白月光留下的、碎成上百片的陶瓷小鸟,修复得完好如初。我以为他会感激,毕竟这是他唯一的念想。可他看到后,却当着我的面,再次将它狠狠砸碎,猩红着眼对我咆哮:「赝品也配碰她的东西?」那一刻,我三年的爱意,连同着满地碎片,彻底燃成了灰。后来,这位高高在上的沈公子疯了似的满......
第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