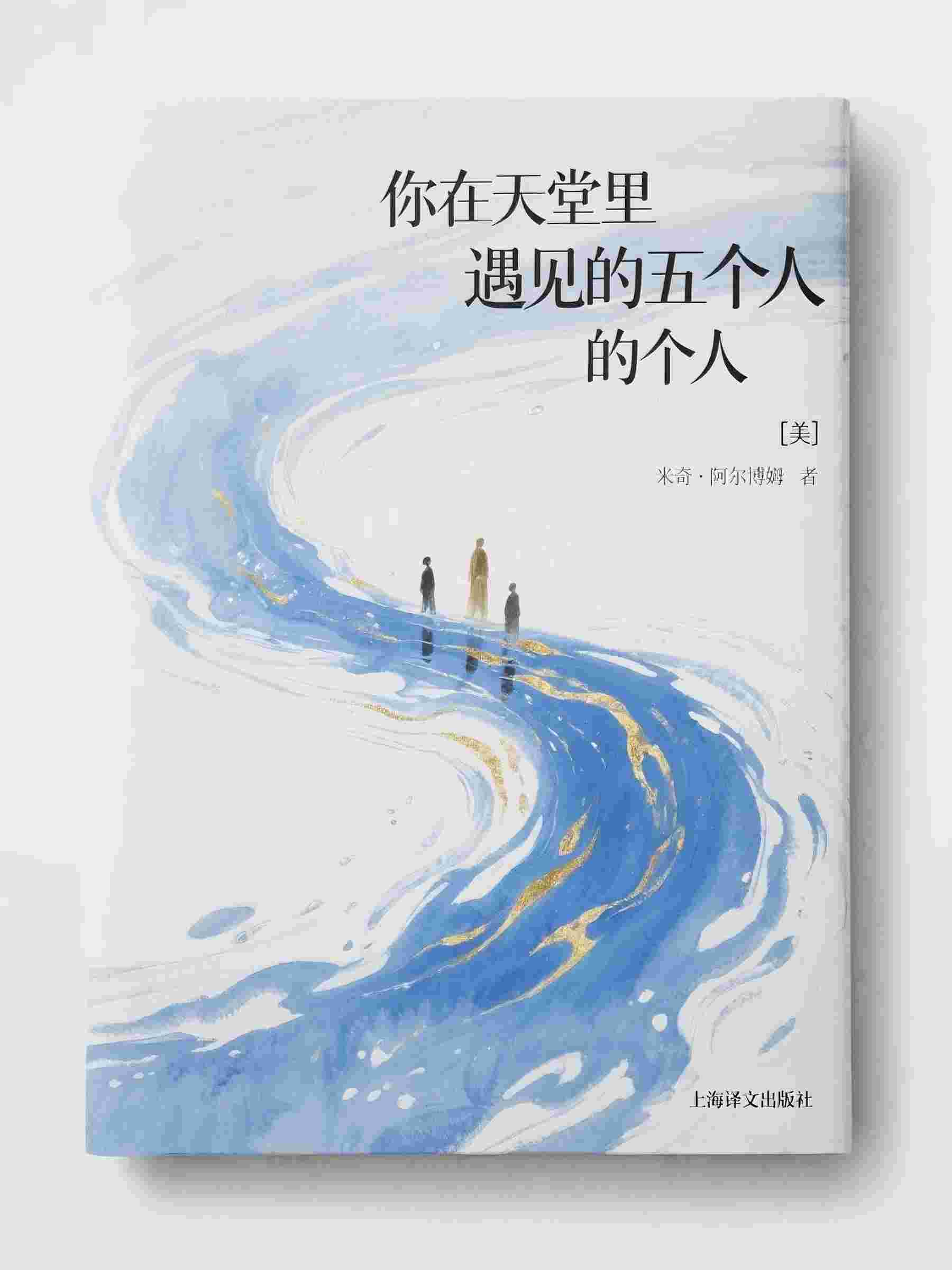顿在“护理重点”那行字上——“观察情绪波动,避免强光噪音,每日协助进行30分钟放松训练”。
她抬头看向李姐:“那他今早的药……我已经让药房提前配好了,放在治疗盘里,八点准时送过去就行。”
李姐拍了拍她的胳膊,眼里带着信赖,“你细心,比我会照看人。
我尽量赶在十一点前回来,这一上午就拜托你了。”
话音刚落,走廊那头传来护士站的呼叫铃,李姐应了声“来了”,又叮嘱了句“他不喜欢别人碰他的私人物品,尤其是床头柜上那个黑皮本子,千万别动”,便转身快步走了。
我捏着那个牛皮本,站在原地往302的方向望了眼。
那间病房在走廊最尽头,门虚掩着,从门缝里能瞥见里面拉着厚厚的遮光帘,只漏进一丝灰蒙蒙的光,静得连隔壁病房的说话声都飘不进去,像个被世界暂时隔绝的小角落。
她深吸了口气,将本子塞进白大褂口袋,转身走向治疗室——得先去把沈砚的晨间药准备好。
我端着治疗盘往302病房走,盘沿的不锈钢被晨间的空调风吹得有点凉,指尖搭在上面,能清晰摸到盘里玻璃药瓶的弧度。
离病房还有两步远时,就觉出不对劲——别家病房这会儿多半敞着窗,晨光混着消毒水的味道漫出来,可这扇门却关得严实,连门缝里都没漏出多少光亮。
推门时,合页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,像是惊扰了什么。
果然,病房里暗得厉害,厚重的遮光帘拉得密不透风,只在窗帘底边和地面的缝隙处,泄进一缕极淡的、近乎灰色的光,勉强勾勒出病床的轮廓。
空气里除了惯常的消毒水味,还飘着点若有似无的雪松香气,大概是病人用的香薰,可被这暗沉的光线一裹,竟透出点压抑的滞重感。
“沈砚先生?”
我放轻脚步,治疗盘在手里稳了稳,声音压得比平时更低,“该晨间用药了。”
病房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,回应我的只有窗帘被风掀起的细微声响。
我又往前挪了两步,离病床更近了些。
借着那点微光,能看见被子隆起一个明显的人形,看轮廓像是缩在床中央,连头都埋在被角里,只露出几缕深黑的发梢。
“沈砚先生?”
我稍稍提高了音量,怕他没听

霸道总裁爱上护士的我全文免费
推荐指数:10分
小宁李姐是现代言情《霸道总裁爱上护士的我全文免费》中的主要人物,梗概:护士李姐踩着护士站的瓷砖快步过来时,白大褂的下摆还带着风,手里攥着的排班表边角都被捏得起了褶。她往小宁面前一站,语气里带着点急茬的恳切:“小林,今天上午你帮我盯下班成不?302床那个高干病人,你替我多照看两眼。”我刚给12床换完输液袋,手背上还沾着点酒精的凉意,闻言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——七点四十五......
第2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