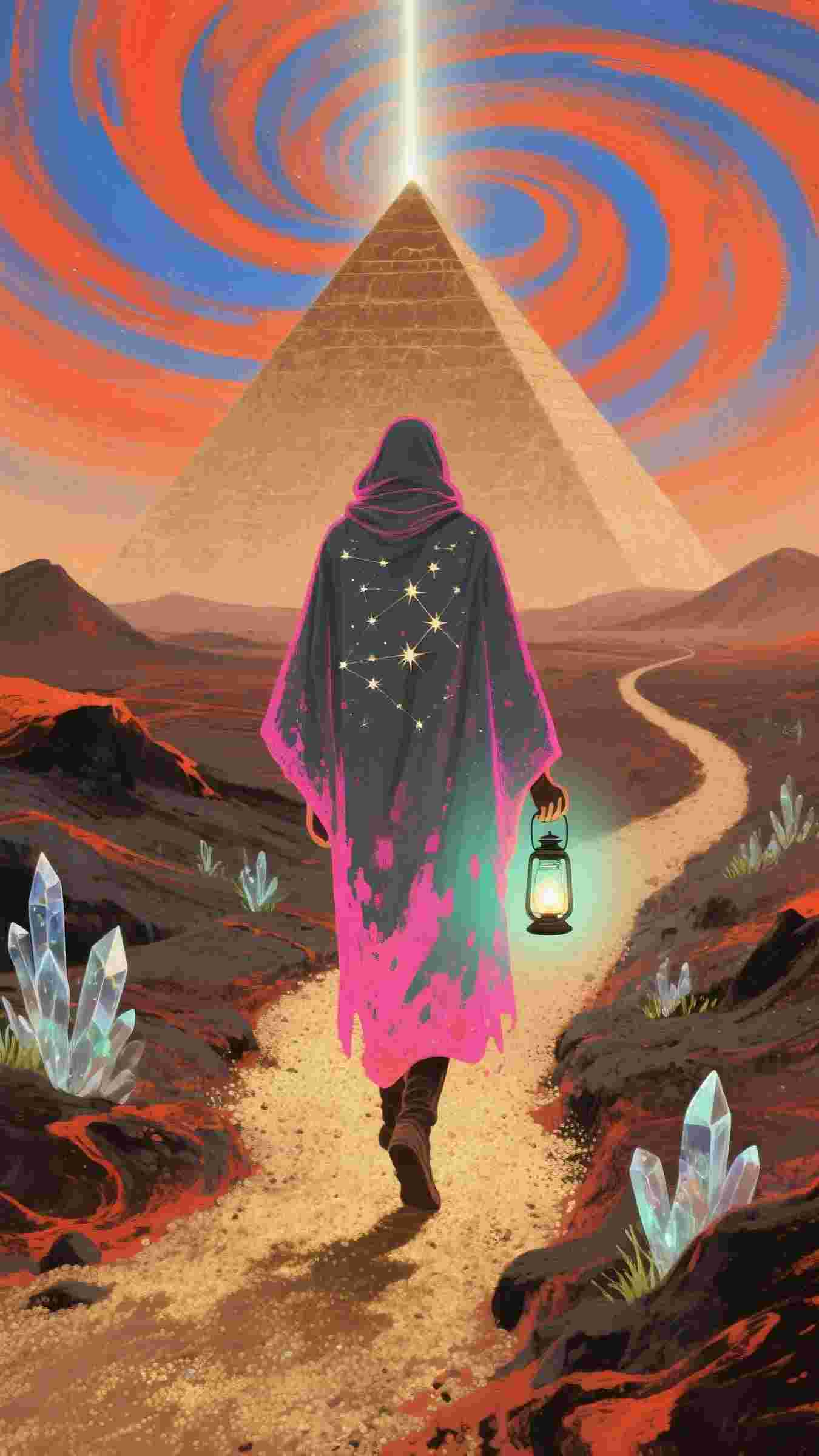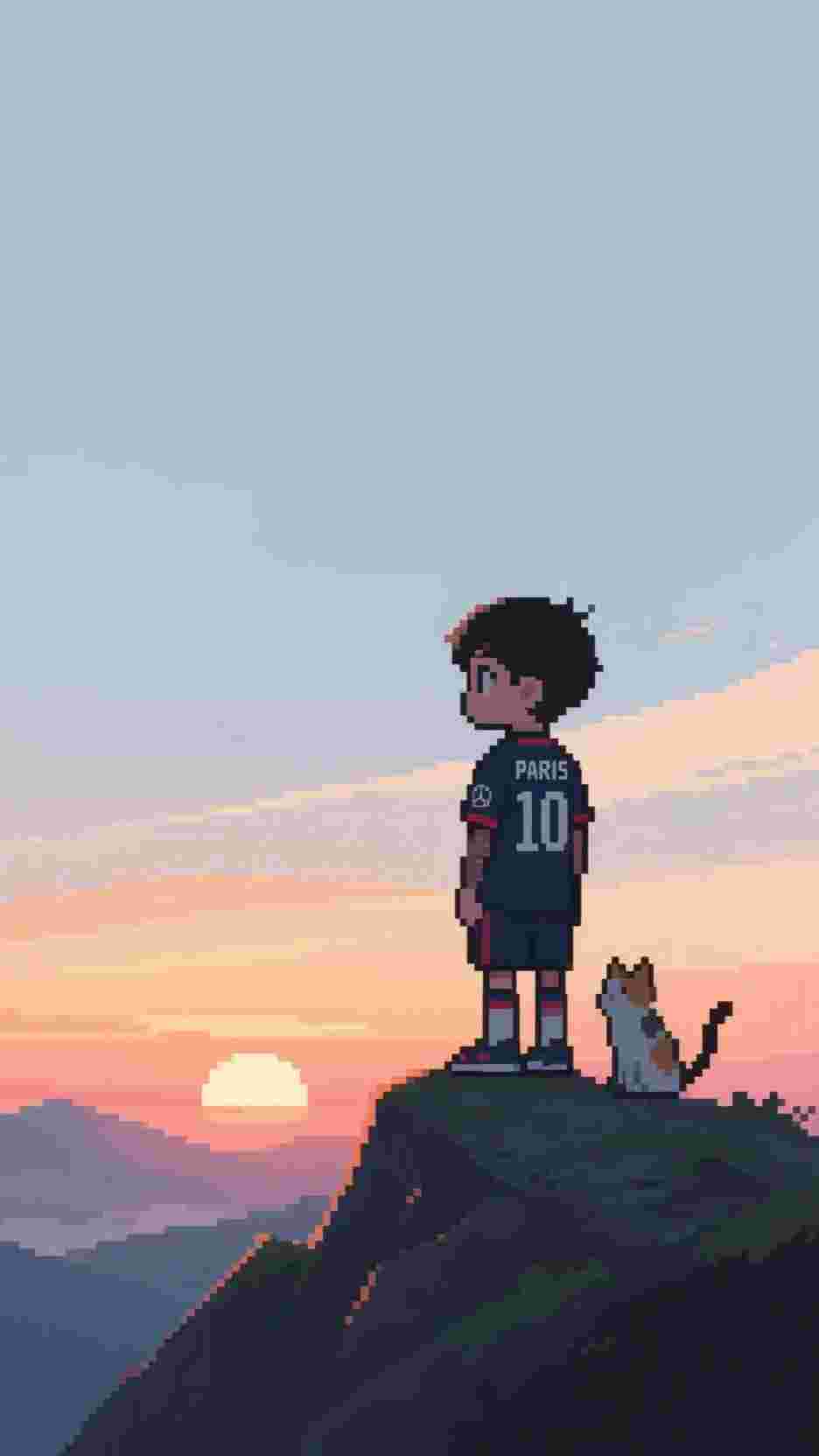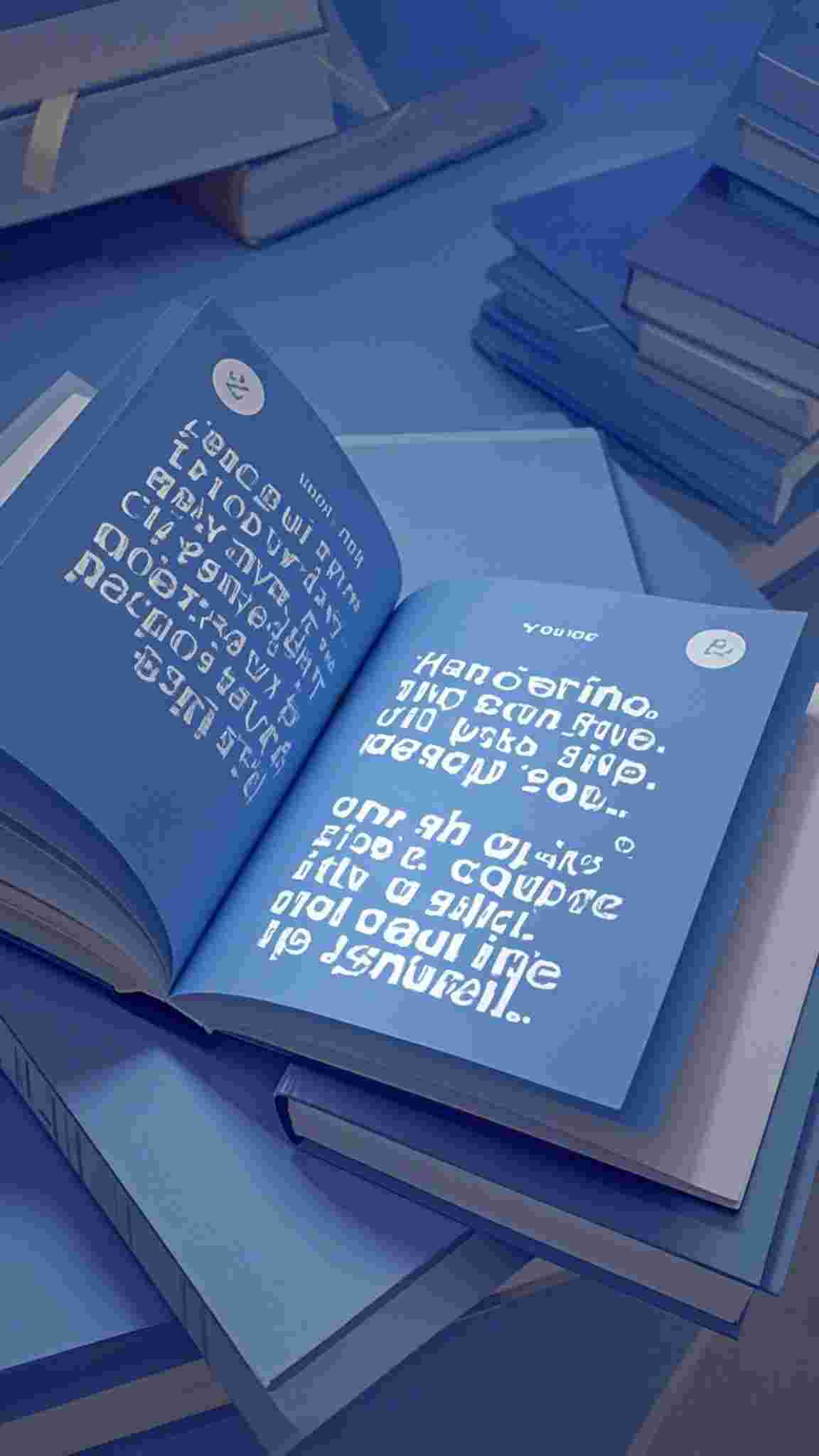空。
“胡虏使节到了!”
传令兵的声音在风中被撕碎。
前方。
一队不过二十人的胡骑如同钉子般钉在河道中间的空地上。
人马皆裹在脏污厚重的皮袍里,只露出一双双浑浊又锐利的眼睛。
雪亮的弯刀并未出鞘,只是沉默地悬在鞍侧。
空气中有种无声的角力。
沉重得能压垮人的呼吸。
马蹄踏在河谷湿滑的卵石上。
我策马出阵。
对面。
一个须发蜷曲、裹着肮脏白色毛皮、眼窝深陷似饿狼的胡骑越众而出。
枯瘦的手勒住躁动的战马缰绳。
他浑浊的眼珠子滚过来,目光钉子一样钉在我脸上。
右手抬起,做出一个极缓慢的、张开五指摊开的古怪手势。
然后不动了。
像是在等候回应。
“大人,不能去!”
身边年轻偏将的声带都在抖,按着刀柄的指节青白,“那是狼王帖木儿!
出名的毒蛇!”
风声在耳畔呼啸。
带着上游尚未融化的冰碴碎屑。
刮得人脸颊生疼。
右眼的视线越过帖木儿,落在他身后那队沉默如同冰雕的胡骑身上。
没有鼓噪,没有谩骂。
唯有一股凝如实质的、属于野兽才有的冰冷杀气,混在寒风里拍打过来。
像暴风雪前最后的死寂。
忽然。
一张脸毫无征兆地撞进脑海。
不是眼前这饿狼般的帖木儿。
是很多年前。
掖州军营外那个大雪的深夜。
一个蜷缩在破席子里等死的胡虏逃兵。
脏污的皮袍和冻僵的脸。
胡虏……被族人丢弃的……逃兵……喉头无声地动了一下。
身体向前微倾。
马镫轻磕马腹。
黑马打着响鼻,迈开四蹄。
踏着河道中冰冷的砾石,一步,一步,迎向那队沉默的狼骑。
没有拔刀。
双手紧握缰绳。
手心里全是冰冷的汗。
蹄铁敲击石头发出的脆响,在巨大的河谷中渺小得如同蝼蚁的挣扎。
在距离帖木儿不到三丈的地方停下。
狂风卷着砂石抽打在双方身上,衣袍猎猎作响。
我和他之间。
只有风在吼叫。
砾石被冻得嘎吱作响。
他深陷的眼窝死死盯着我。
右手摊开的手掌纹丝不动。
像一尊泥塑。
浑浊眼珠里没有任何属于人的情绪,只有一种原始的、评估猎物般的冰冷审视。
时间如同被拉长。
每一息都像塞北的寒冬一样漫长煎熬。
身后的己方阵地上,年轻偏将急促的呼吸声几乎能穿透风声。
对

锦月如歌.禾晏独白(番外)+(全文)
推荐指数:10分
小说《锦月如歌.禾晏独白(番外)+(全文)》新书正在积极地更新中,作者为“白昼岛”,主要人物有晏儿黄毛,本文精彩内容主要讲述了:1那碗药很烫。褐色的药汁在豁口粗陶碗里晃,氤氲的热气蒙住了阿娘蜡黄的脸。她的手枯瘦得像隆冬的槐树枝,从补丁摞补丁的旧被子里伸出来,颤巍巍地够碗沿。指尖冰凉,碰着我被碗烫得发红的指头,猛地一缩。“晏…晏儿,”阿娘的声音像破风箱,气短得连不成句,“冷……窗……”北风裹着碎雪粒子,正顺着糊窗棂的旧纸破洞往......
第19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