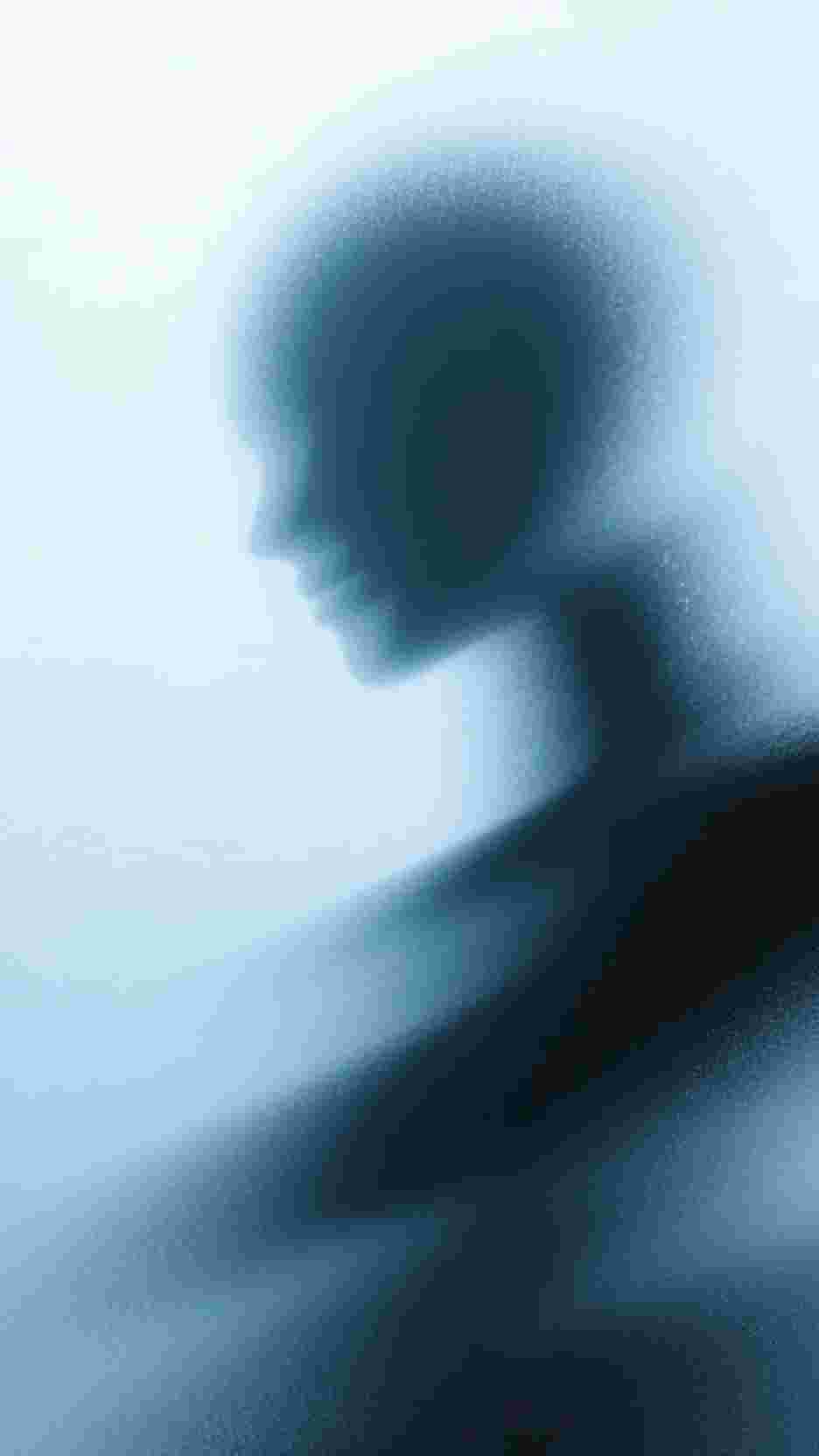时无刻不在散发着阴冷气息的琵琶旁边。
它的“需求”与日俱增。
起初只是偶尔的、轻微的嗡鸣,像饥饿的胃袋在空虚地抽搐。
但很快,那嗡鸣变得频繁而焦躁,琴身那暗红的色泽也开始变得不稳定,时而黯淡如干涸的血痂,时而又流转欲滴,散发出更浓重的血腥冷香。
它在催促。
那种无形的压力再次降临,比上一次更沉重,更不容抗拒。
它挤压着我的胸腔,攥紧我的太阳穴,冰冷的意志顺着脊椎爬行,试图再次操控我的手臂,去触碰那渴望饮血的弦。
我死死咬着牙抵抗,指甲抠进掌心,掐出深深的印痕。
冷汗浸透了我的衣衫,又很快被一种从骨头里渗出的寒意冻干。
不能碰。
绝对不能再碰。
每一次触碰,都是在将自己的灵魂更深入地抵押给那个可怕的存在,都是在用他人的性命来延续我这苟延残喘的、已然污秽不堪的生命。
可是,那无声的催促越来越强。
第三天夜里,嗡鸣声已经尖锐到像是无数根冰冷的针,持续不断地刺扎着我的耳膜和神经。
桌上的茶杯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,房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。
整个屋子都在那无声的索求中轻微震颤。
我蜷缩在角落,用破旧的棉被死死捂住头,牙齿咬得格格作响,几乎要碎裂。
抵抗的代价是意识开始模糊,眼前出现各种扭曲的幻象——那张咧至耳根的流血巨口,那双黑洞洞的、毫无感情的眼睛,还有阿川和那个戏子干瘪带笑的脸,他们在无声地尖啸。
就在我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要彻底崩溃,要么疯掉,要么被迫再次伸出手时——屋外,极其遥远的地方,突然传来了一丝极细微、极飘忽的声响。
像是……有人在哼唱。
断断续续,不成调子,沙哑而苍老,却固执地穿透了这厚重的、令人窒息的死寂屏障,微弱地传了进来。
是镇东头那个又疯又哑的老乞丐婆!
她平时就疯疯癫癫,睡在破庙烂檐下,偶尔会发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呓语和嘶吼。
全镇恐怕只有她,因为彻底的疯癫和与世隔绝,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恐怖,也不知道保持寂静的生禁令。
她那无意识的、沙哑的哼唱,在这片绝对的死寂里,简直如同惊雷一般刺耳!
几乎就在那哼唱声传来的瞬间——

田都元帅的禁忌祭品抖音热门:全章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田都元帅的禁忌祭品抖音热门:全章+后续》,讲述主角抖音热门的甜蜜故事,作者“冀州小吏”倾心编著中,主要讲述的是:1 破庙琴杀南管的音律像是从极幽深的时间裂缝里渗出来的,呜咽缠绵,每一个音符都拖着古老潮湿的尾调,钻入耳膜,缠紧心脏。我被那乐声引着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夜雾弥漫的青石板路上。两侧黑瓦灰墙的屋舍门窗紧闭,死寂无声,只有这诡谲的丝竹声,和我腕间那对银镯子冰凉的撞击声,在湿漉漉的空气里一下下敲着。我是祭品......
第12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