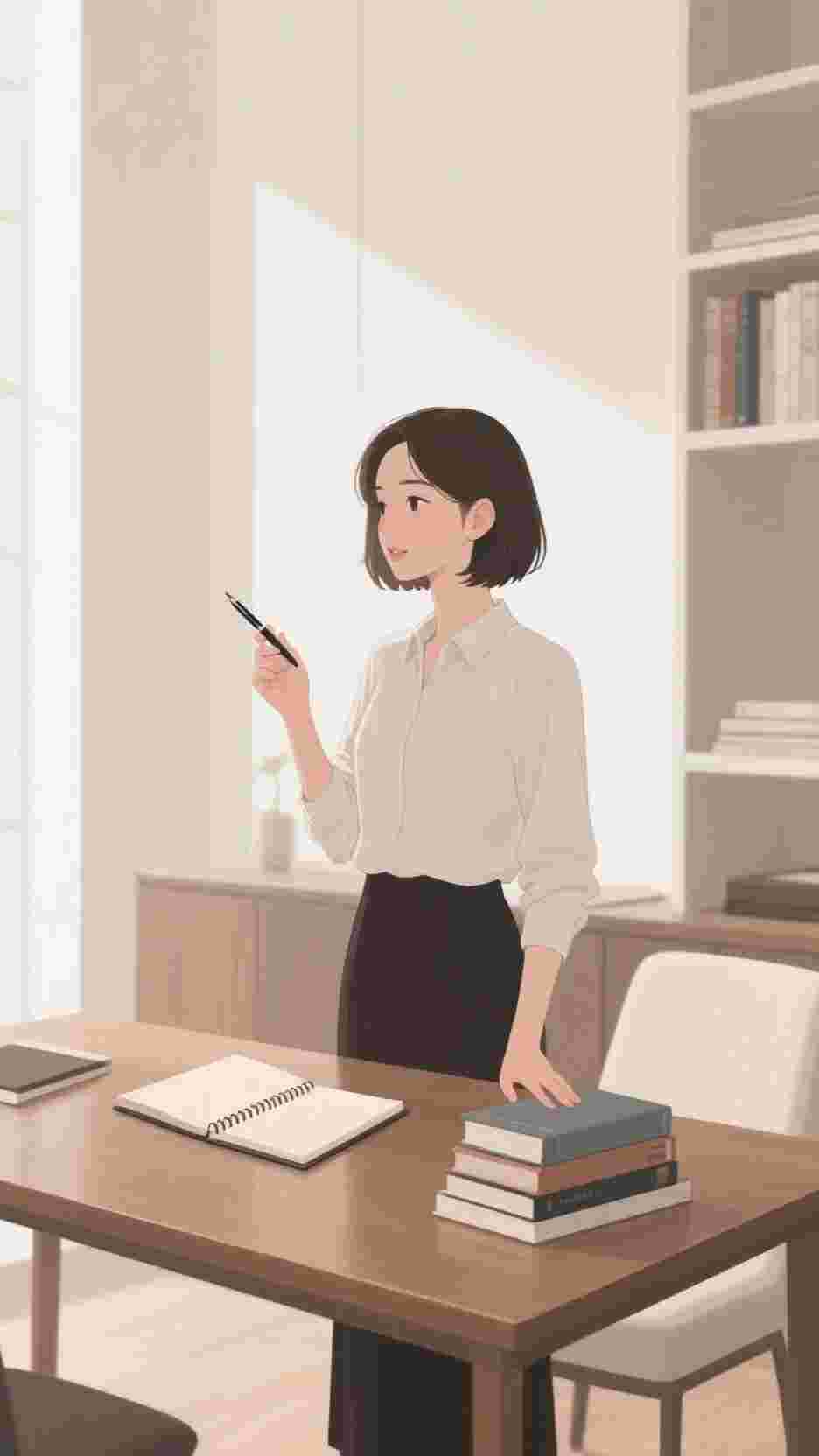碎的玻璃渣,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地面,没有一块能拼凑出完整的形状。
我感到的不是心痛,也不是委屈,而是一种彻底的荒谬感。
为他们,也为自己。
我耗尽心血构筑的防火墙,最后被这群人用最原始、最荒诞的方式,从内部瓦解了。
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浸满了汽油的棉花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痛。
我慢慢地、极其缓慢地站起身,椅子腿与地面摩擦,发出一声短促刺耳的“吱嘎”,刺破了那层虚伪的寂静。
“我的东西,”我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来,出乎意料地平稳,“我会整理好。
交接文档,在部门共享盘,‘待离职员工’文件夹里。”
我的视线再次扫过郑钱生那张肥硕的脸,“很详细,包括那些‘没用’的模块关键逻辑。”
最后两个字,我咬得很轻,却带着千钧之力。
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,我转过身,推开那扇沉重的会议室玻璃门。
门外的光线涌进来,有点刺眼。
身后,是彻底的、凝固的真空。
关门的声音很轻,“咔哒”一声落下,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句号,彻底斩断了这荒谬的六年。
也许,我“自由”了。
海南的空气像温热醇厚的酒浆,带着海盐的微咸和浓烈阳光的气息,扑面而来,瞬间浸透了肺腑,也仿佛融化了骨头里沉积许久的、来自北方的阴霾与寒意。
我在三亚湾边上租了个推开窗就能扑进海浪的小公寓。
褪色的木地板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,赤脚踩上去,舒服得让人叹息。
手机?
那只陪伴了我多年、记录了无数加班夜晚和嘈杂会议、最终也记录下那份冰冷“民主票选”结果的黑色方砖。
在抵达这里的第一秒,就被我彻底扒掉了SIM卡,连同那张象征着过去六年枷锁的工卡一起,随手扔进了床头柜最深的角落,仿佛丢弃两块滚烫的烙铁。
世界一下子安静得像被蒙上了厚厚的天鹅绒。
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刻度。
日头像个慷慨的主人,肆意挥霍着金箔般的光线。
我醒了就跳进清澈得能看到脚趾的海水里泡着,或者租一艘晃晃悠悠的小渔船,跟皮肤黝黑、笑容淳朴得像礁石一样的老周出海。
老周话不多,递给我渔线时,眼神里只有对大海熟稔的平静。
“阿峰,手上茧子硬,是个实

我被公司裁员了全文无删减
推荐指数:10分
《我被公司裁员了全文无删减》是作者“五十老仙”的代表作,书中内容围绕主角李曼林峰展开,其中精彩内容是:公司民主投票决定裁员对象,不善喝酒搞关系的我被票选出局。我默默飞往海南关机度假,二十天后开机发现99 未接来电。老总在语音里歇斯底里:“系统瘫痪了!十倍工资求你回来!”我笑着再次关机,任凭公司天翻地覆。直到那个曾当众拍我肩膀说“技术宅没用”的胖老总,满头大汗,出现正惬意躺在沙滩上我的面前。他颤抖着递......
第3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