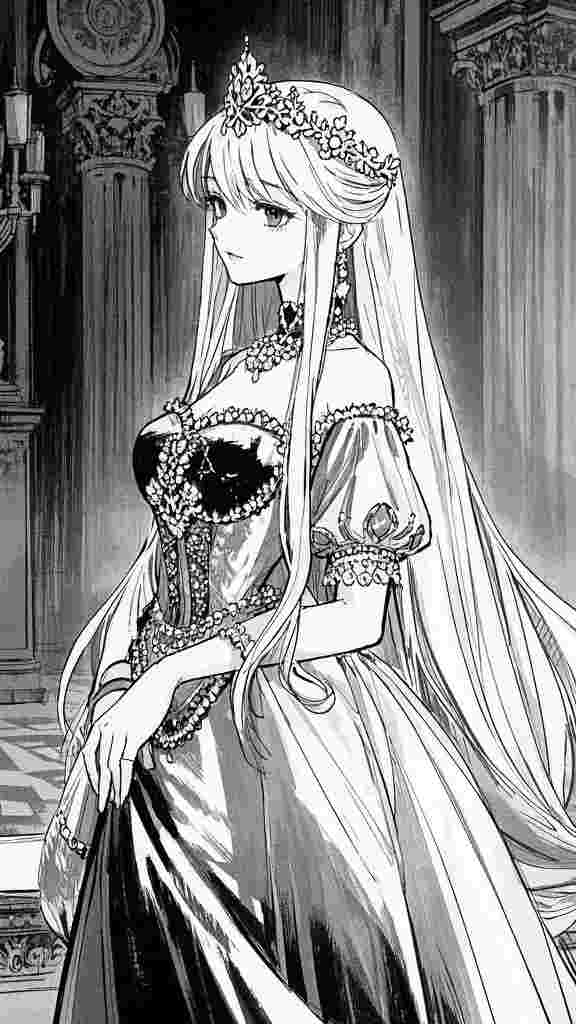的瞳孔,声音不高,却字字如冰锥,带着一种穿透灵魂的狠戾,清晰地钻进我耳朵里,也钻进每一个竖着耳朵的旁观者耳中:“江临,记住你今天的话。”
她顿了顿,每一个音节都淬着剧毒,“好好记着。
一个字,都别忘。”
说完,她甚至不再看我一眼,仿佛我只是脚下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。
她微微侧身,墨绿色的裙摆划过一个冷冽的弧度,高跟鞋踩在冰冷的地砖上,发出清脆又决绝的“哒、哒”声,径直从我身边走过。
那缕清冽又带着烟草味的冷香,如同最锋利的刀锋,刮过我的鼻尖,留下火辣辣的痛感。
我僵在原地,像一尊被瞬间抽空灵魂的泥塑木偶。
大脑一片空白,耳边嗡嗡作响,只剩下她那句淬毒的话在疯狂回旋——“记住你今天的话……好好记着……一个字,都别忘……”露台门口的人群下意识地为她分开一条道路。
无数道目光,带着震惊、怜悯、幸灾乐祸,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,聚焦在我脚下那两片刺眼的白色碎纸上。
脸上火辣辣地烧起来,比被人当众抽了几十个耳光还要难堪。
一股强烈的、被扒光示众的屈辱感,混合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,如同冰冷的海水,瞬间没顶。
她走了。
背影消失在宴会厅璀璨的光影里,决绝得像从未出现过。
而我,江临,成了这个夜晚最大的笑话。
那晚之后,“支票门”成了圈子里经久不衰的笑谈。
江临被“旧衣服”当众撕碎支票羞辱的细节,在无数个私人会所、酒局牌桌上被添油加醋地演绎传播。
我的名字,和“自作多情”、“脸被打肿”这些词牢牢捆绑在了一起。
日子变得面目可憎。
酒精成了唯一能麻痹神经的东西,可越喝,脑子里那双淬毒的眼睛就越清晰。
温念两个字,像刻在骨头上的诅咒,日夜啃噬。
我开始疯狂地搜集关于她的消息,像个病态的偷窥者。
她创办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,名字叫“归栖”,短短半年,几款主打设计横扫了业内几个重要奖项,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锐设计师。
她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温顺的、依附于我的影子。
她变得锋利、耀眼,像被打磨出最璀璨光芒的钻石。
每一次看到财经杂志上关于她工作室融资成功

渣了前任她成我高攀不起的白月光江临温念完结文
推荐指数:10分
《渣了前任她成我高攀不起的白月光江临温念完结文》这部小说的主角是江临温念,《渣了前任她成我高攀不起的白月光江临温念完结文》故事整的经典荡气回肠,属于现代言情下面是章节试读。主要讲的是:我叫江临,圈里出了名的浪子,却栽在了温念手里。分手那天我甩给她支票:“你这种女人,配不上我的真心。”她笑着撕碎支票,眼神淬毒:“江临,记住你今天的话。”后来我在拍卖会一掷千金博她一笑,她挽着新欢问我:“江先生哪位?”我跪在暴雨里砸门:“念念,我把命给你好不好?”门开了,她指尖夹着烟轻笑:“晚了,你的......
第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