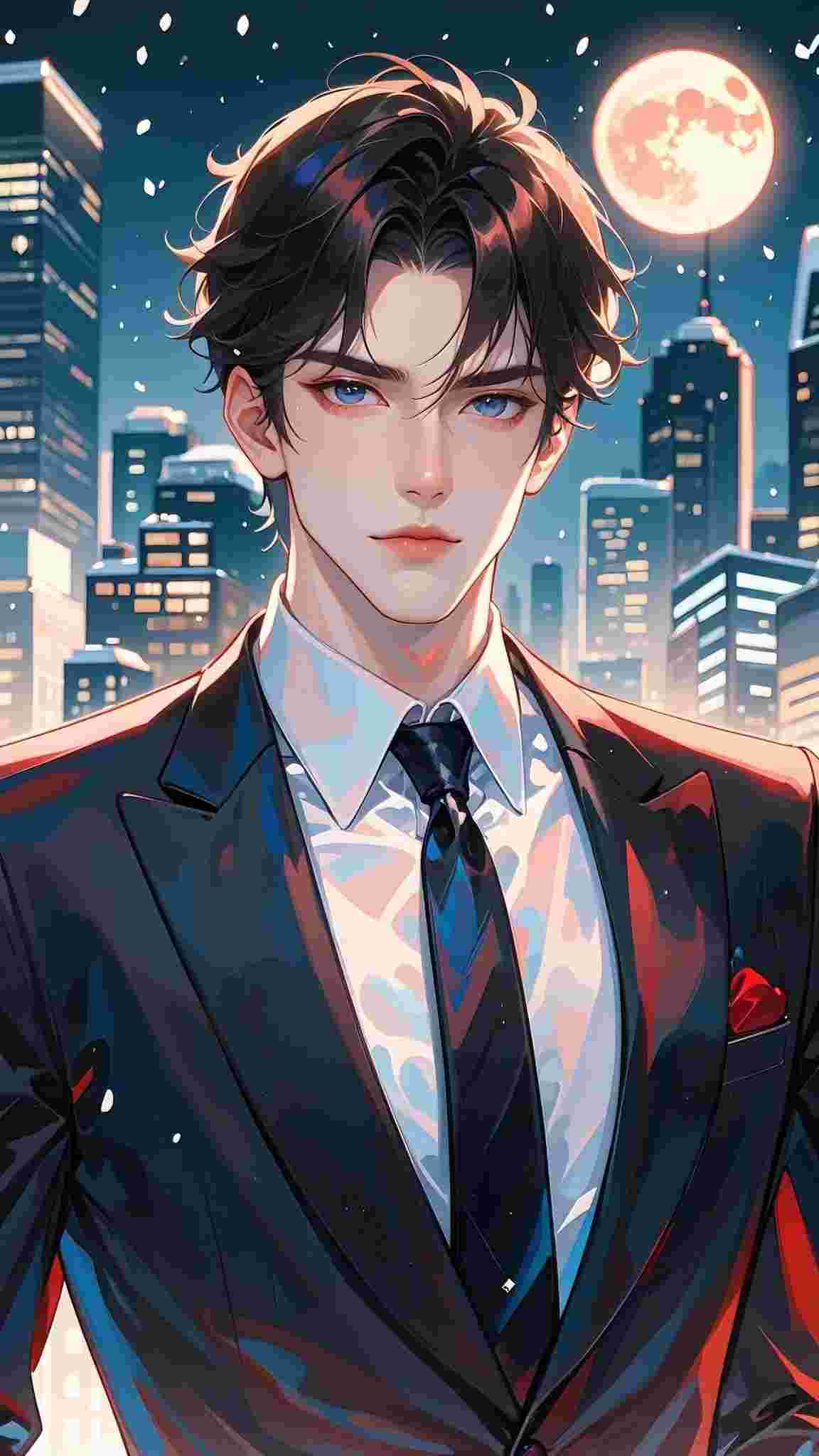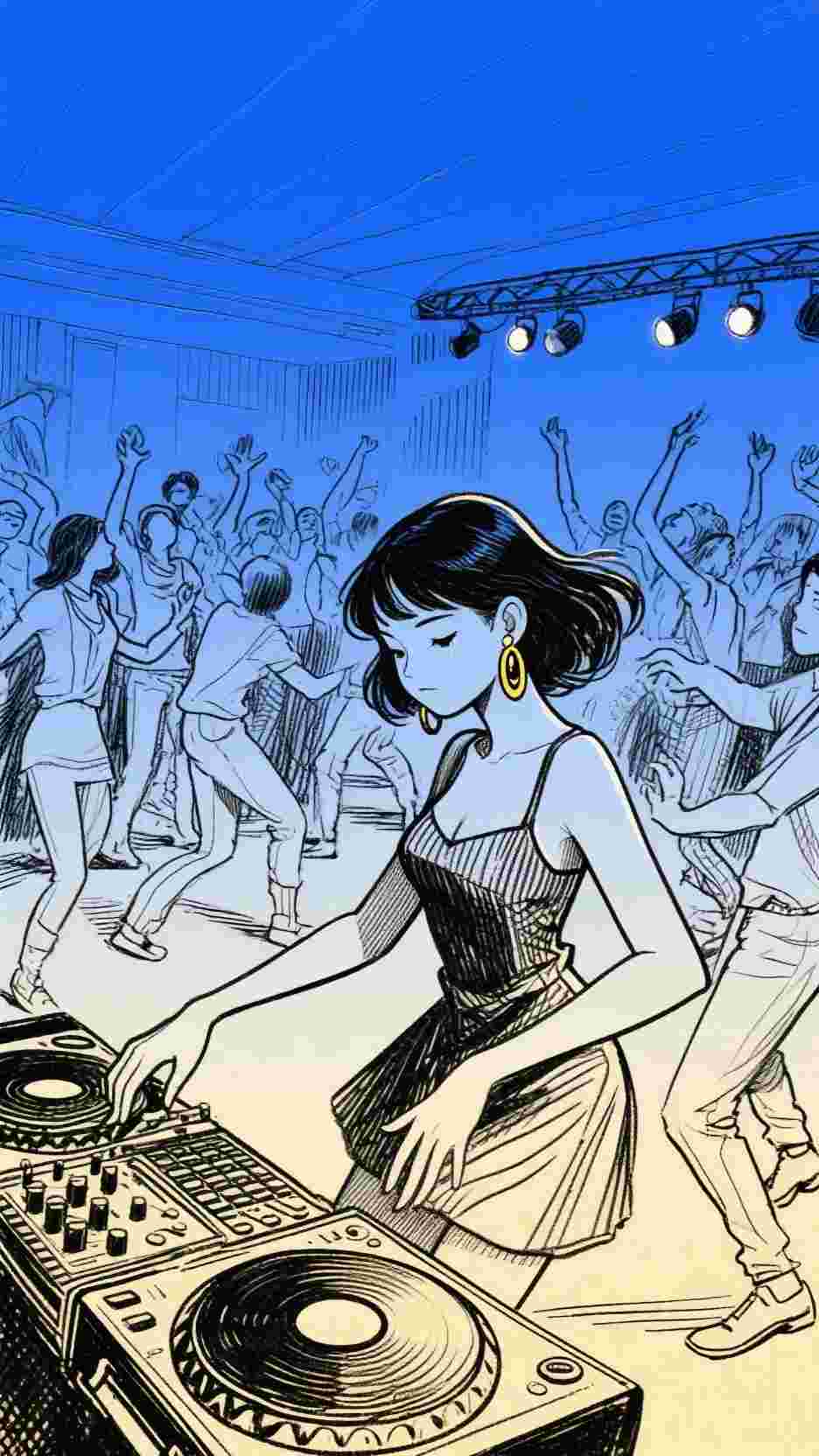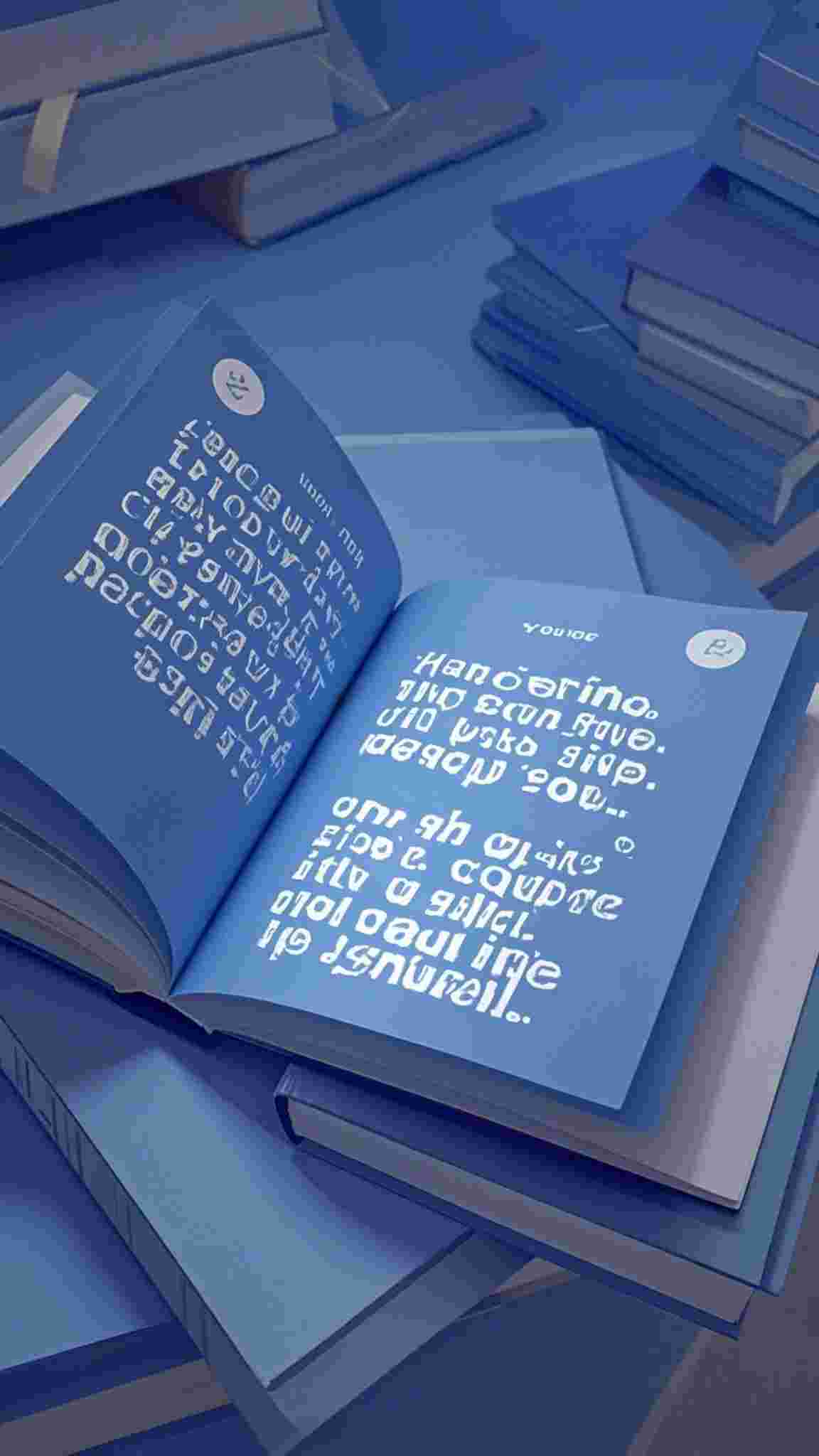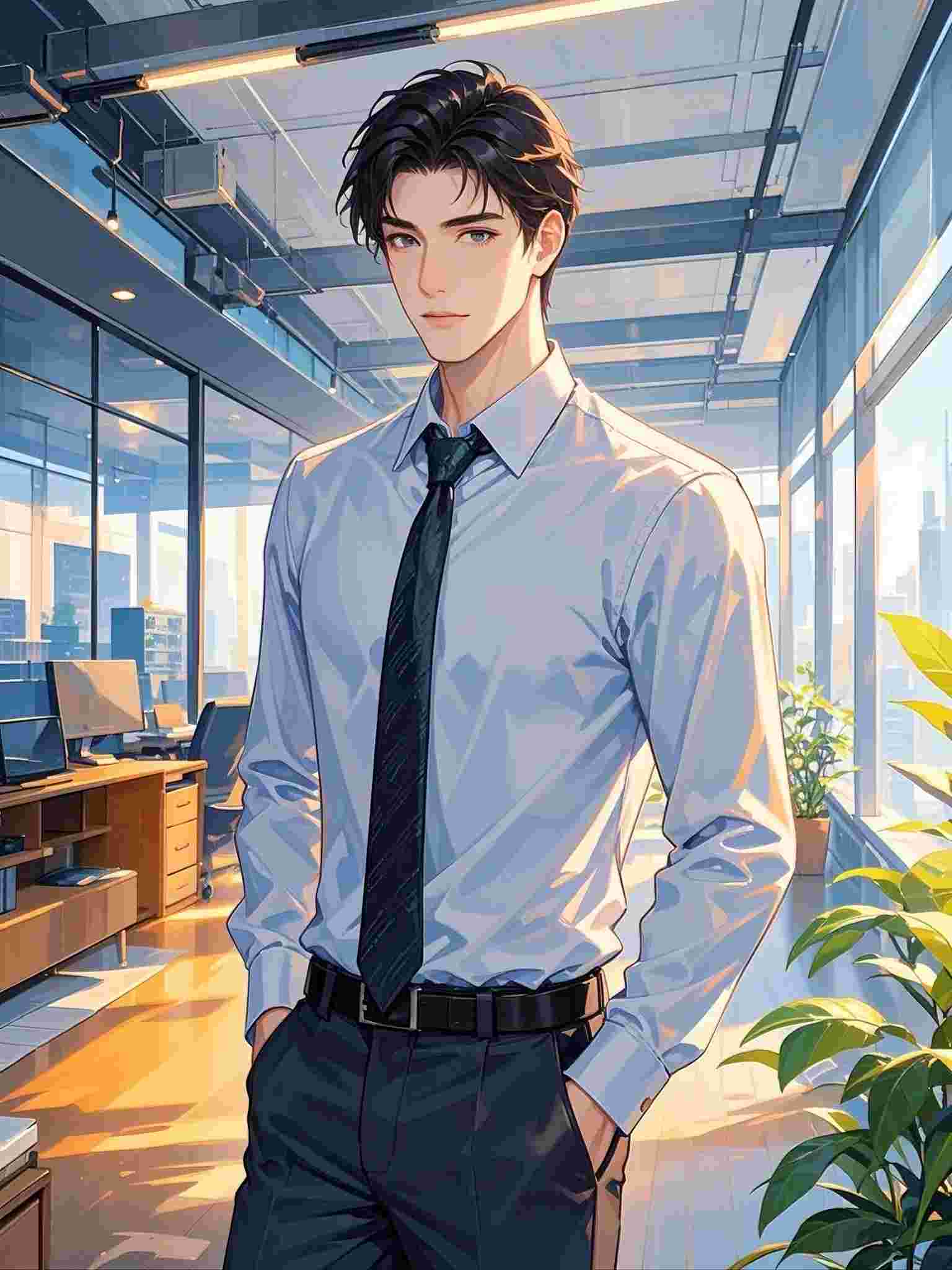实感,往往得从柴米油盐开始。
这叫‘人味’。”
第二天一早,一辆低调的黑色SUV停在小区门口。
司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,皮肤黝黑,眼神沉稳,叫我“苏小姐”,介绍自己叫老周,本地开了十几年出租,路熟。
后座上果然放着几袋优质米和油。
老周话不多,但极其靠谱。
在他的指引下,我们没有去项目部,而是拐进了项目地块边缘的一个自然村。
村子半新不旧,一些自建小楼夹杂着老屋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。
我把傅沉给我准备的名牌套装和高跟鞋换成了简单的T恤牛仔裤和平底鞋,头发扎成马尾,没化妆。
村口小卖部门口,几个老人坐着下棋,看到陌生车辆,眼神里带着警惕。
我让老周在远处等着,自己拎了一桶油,走过去,露出一个略带疲惫的笑:“大爷,打听个事儿呗?
听说这边要搞大开发,房价是不是要涨啊?”
一个大爷抬眼皮瞅我:“咋?
想买房?”
“哪买得起啊!”
我摆摆手,语气抱怨,“原来在市里上班,累死累活挣那点钱,全贡献给房东了。
听说这边以后发展好,想着来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老房租一间,通勤远点就远点,好歹压力小点。
结果一看,这架势……好像也没戏了?”
我适时地露出失望和茫然。
这套说辞,精准地戳中了一个“外来打工仔”和“潜在被拆迁户”之间的微妙共情点。
另一个大爷叹了口气:“姑娘,别想了,这地儿啊,以后指不定咋样呢。
闹心!”
“啊?
为啥啊?
不是大公司开发吗?”
“大公司?
哼!”
最开始说话的大爷冷哼一声,“坑人的公司!
说好的条件,变来变去!
俺家那点果园,赔那点钱,够干啥的?”
“就是!
俺们老祠堂那边,说是什么风貌协调区,补偿标准压得低低的!
那可都是祖上传下来的!”
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。
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,抱怨、愤怒、无奈、担忧。
我安静地听着,偶尔插一句“这也太坑了”、“那以后怎么办啊”,引导他们说出更多。
真相远比文件上的“模糊条款”更具体,更鲜活,也更……扎心。
中午,我让老周把米和油分给了村里几户看起来最困难的老人家,只说自己是来做公益

重生后,大佬她只想咸鱼打脸后续+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重生后,大佬她只想咸鱼打脸后续+全文》是由作者“尉迟雪”创作编写,书中主人公是张薇苏晚,其中内容简介:(一) 重生掀桌心脏骤停的剧痛还残留在神经末梢。我猛地睁开眼,会议室顶灯惨白的光线刺入瞳孔。耳边是市场部总监张薇冰冷的声音,每一个字都和记忆深处那个索命的魔咒严丝合缝:“……这个文旅城项目的可行性报告,就交给苏晚。周五之前,我要看到详细方案。完不成,”她顿了顿,锐利的目光透过金丝眼镜射向我,带着毫不......
第11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