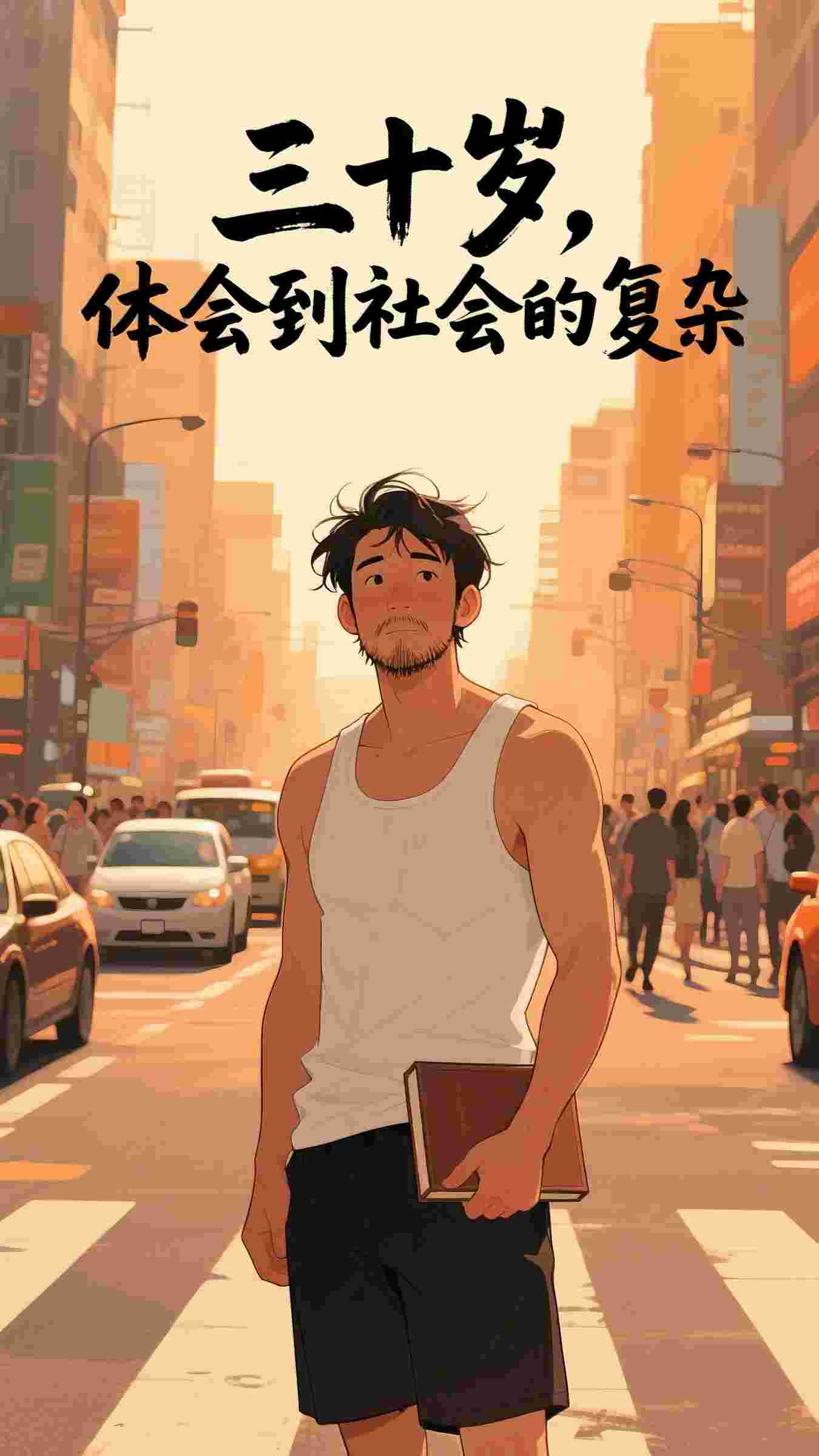院子里撒了一把波斯菊的种子,阿九蹲在旁边松土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曾这样蹲着,只是那时的我,从没被允许靠近。
生产那天,我痛了十六个小时。
阿九守在产房外,听说他抽了自己一耳光,嫌没早点让我少受点苦。
当我听见那声清亮的啼哭,整个人像被泡在温水里,所有的疼都化成了泪。
护士把襁褓放在我枕边,粉团团的小脸皱得像没展开的豆荚。
我轻轻碰她的鼻尖,小声说:“朵朵,我是妈妈。”
<十朵朵三个月就会笑,五个月会翻身,十个月“哒哒”地满屋爬。
阿九给她做了木头学步车,四个轱辘吱呀吱呀,像小火车。
我笨手笨脚地给她缝小裙子,针脚大得能跑火车,她却穿着在院子里转圈,小黄狗跟在后面摇尾巴。
我给她讲我的故事,讲到流浪时,她眨巴着眼,把手指塞进我嘴里:“妈妈,吃糖。”
那是一颗化得黏糊糊的奶糖,不知什么时候藏在她围兜兜里。
我咬了一口,甜得发苦,眼泪砸在她手背上。
朵朵慌了,用小手给我擦:“妈妈不哭,我乖。”
阿九在厨房煮面,探出头笑:“咱闺女比你懂事。”
我瞪他,却忍不住弯了嘴角。
十一朵朵三岁那年,我们攒够了首付,在城西买了套小两居。
搬家那天,我把那张最初的糖纸——已经被摩挲得发白,边缘起了毛边——郑重地贴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,旁边挂上朵朵画的全家福:三个歪歪扭扭的圆圈,中间的小圆扎着冲天辫。
夜里,我坐在阳台,看远处万家灯火。
阿九从背后环住我,下巴抵在我头顶。
我们谁都没说话,却听见彼此心里“咚”地一声——那是漂泊了一辈子的船,终于靠岸的声音。
十二朵朵五岁了,上了幼儿园。
第一天放学,她举着一张皱巴巴的画,扑进我怀里:“妈妈,今天老师让我们画‘家’。”
画上是三棵树,最矮的那棵开着一朵巨大的红花。
我蹲下来,和她鼻尖碰鼻尖:“为什么这朵花这么大?”
朵朵奶声奶气:“因为它是妈妈!
妈妈叫小花,小花要开得最大!”
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九岁的自己,蜷在稻草堆里,也曾把“小花”两个字写在雪地上,等一场不会来的回头。
如今,我的小花

花又一次开了抖音热门全集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花又一次开了抖音热门全集》,讲述主角抖音热门的爱恨纠葛,作者“凌梦初”倾心编著中,本站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:我叫小花。他们说,这两个字写起来简单,念出来也轻,像风里一吹就散的蒲公英。可我却用了整整一生,才把它写得端正、写得温热。一我出生那天,屋外下着连绵的细雨。母亲疼得咬破了嘴唇,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。雨声、哭声、烟雾缠在一起,像一团乱麻。后来麻团散了,我来了。父亲掐灭烟头,笑着说:“就叫小花吧,好养活。”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