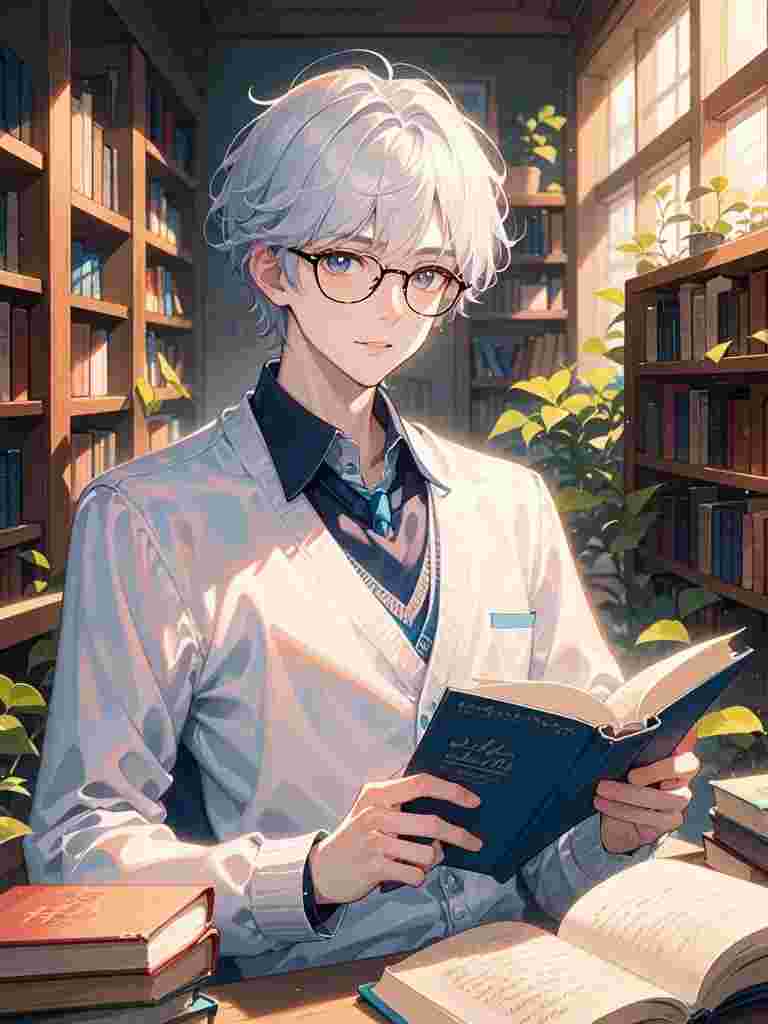亲常去牌场喊父亲回家,没少吸那些污浊空气。
母亲临终前,拉着父亲的手说:“满仓,我走了,没人管你了,但你要照顾好建国,别整天扑在牌桌上。”
父亲哭得像个孩子,连连点头。
母亲下葬后,父亲确实消停了一段时间。
但不过三个月,他又坐回了牌桌前。
他说:“建国,我心里空,只有打麻将时才能不想那些难受的事。”
陈建国没说什么,他知道,对父亲而言,麻将不只是娱乐,更是一种逃避和寄托。
后来陈建国考上大学,离开家乡,毕业后在省城安了家。
他几次接父亲到城里住,老人总是待不到一个星期就嚷着要回去。
“城里没人打麻将吗?”
陈建国问。
“有是有,但不一样。”
老陈头摇头,“村里的麻将,打着打着能吵起来,吵完了又笑呵呵一起喝酒。
城里的麻将太安静,没味道。”
于是老陈头又回到村里,继续他雷打不动的麻将日程。
村民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存在——每天午饭后,总能看见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拎着泡满枸杞的保温杯,慢悠悠走向村活动中心的牌场。
“吃饭了吗?”
路上遇到人,他总是这样打招呼,不等对方回答就接着说,“我吃过了,去打两圈。”
仿佛那不是娱乐,是一份正经工作。
老陈头牌技一般,手气更差,十打九输。
牌友们开玩笑说:“老陈头一来,咱们今天的饭钱就有了。”
他也不恼,嘿嘿一笑:“娱乐第一,输赢第二。”
但其实他在乎输赢,每次摸到好牌,眼睛就发亮;要是一直输,就一支接一支抽烟,愁眉不展。
牌友们都知道他这个毛病,常故意逗他:“老陈头,今天输多少了?
要不歇歇?”
“歇什么歇!
牌场如战场,不能当逃兵!”
他总是这样回答,然后更加专注地盯着牌桌。
陈建国劝过他多次,年纪大了,少打麻将少抽烟。
老陈头当面答应得好好的,一转脸又忘得一干二净。
<“爸,您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。”
陈建国每次回家都劝。
“我都这把年纪了,还能活几年?
让我痛快痛快不行吗?”
老陈头总是这么说,眼睛盯着电视里的戏曲节目,手指却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着,仿佛在摸牌。
陈建国无奈,只能由着他

最后一把胡牌无删减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叫做《最后一把胡牌无删减全文》的小说,是一本新鲜出炉的现代言情,作者“丘胜”精心打造的灵魂人物是陈建国建国,剧情主要讲述的是:老陈头死在了牌桌上,胡了一把字一色单钓。消息像夏天的野火,迅速在陈家村蔓延开来。人们交头接耳,议论纷纷,却都不觉得特别意外。“老陈头啊,到底是这么走了。”村头小卖部的老王叹了口气,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包红塔山,抽出一根点燃,仿佛在祭奠什么。陈建国接到电话时正在工地上扛水泥。八月的日头毒辣,汗水沿着安全帽......
第3章